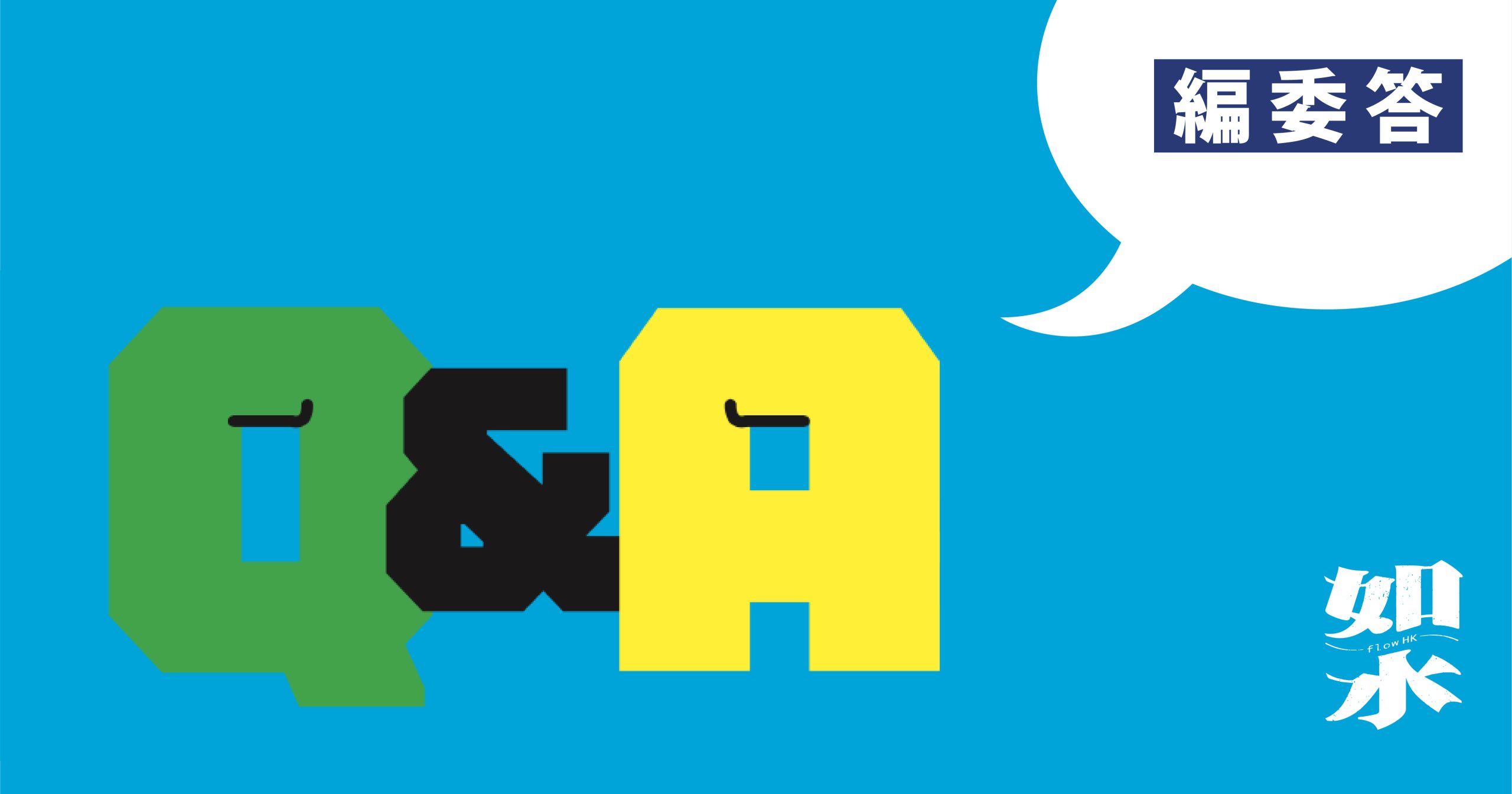《如水》第九期編委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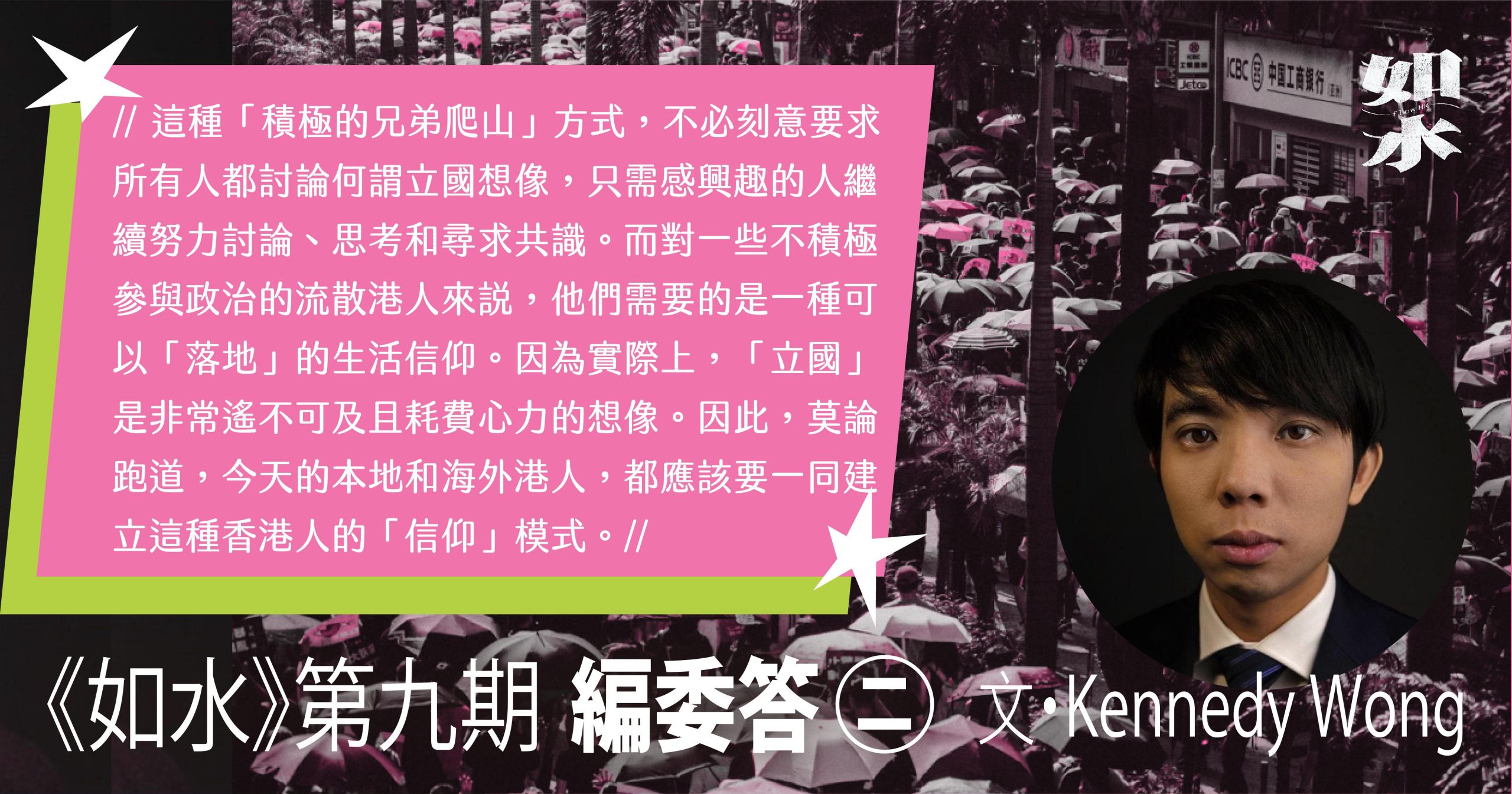
(編按﹕《如水》每期均會邀請讀者向編委直接發問各種問題。收集問題後,編輯部將加以整理,並轉交編委回應。任何人士均可發問,有意者可按此。)
讀者:如有天時地利,香港可以立國,人和方面可以怎樣準備?對在港或離散港人,公民教育在 2019 年全民覺醒後,進展比較緩慢,當然仍有非常多的有心人在努力,我也很鼓舞,但 mass population 對立國沒有基本想像,可能限制了其發展進程,編委們有甚麼看法?
Kennedy Wong:「你想要一個點樣嘅香港社會?」 ——立國想像與公民信仰
非常感謝讀者的問題!在寫這段回應的時候,立法會 47 人案件正在審訊,有當日的同路人變成污點證人,不論身在香港,還是流散各地的香港人都百感交雜,帶著苦痛、無奈、憤怒等。提到立國,不論現實的基礎,還是公民的想像,不少人在這個時候都會覺得絕望、沒有可能。與此同時,不少人會擔憂時間會慢慢磨掉香港人的群體性,更難以延續和交棒給下一代。這就是今天香港人的兩難。
再思「反抗共同體」
那麼我們先說說今天的香港人是如何找到聯繫方式。自 2019 年,不少人會提出,香港人團結的原因是痛苦與反抗。用梁繼平的說法,這是「痛苦的共同體」。他參考的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於國族(Nation)想像共同體的理解。在 2019 年 8 月 16 日一場遮打花園的「英美港盟 主權在民」集會中,梁曾經講到「所謂的共同體,就是能夠想像他人之痛苦,並且甘願彼此分擔的群體」。面對痛苦而產生的情感意識,可以跨越某程度的分歧,以做到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篤灰、不割席、不分化」。諸位讀者活在今天,回望這些口號,難免會百感交雜。
其實,近來轉為「污點證人」的區諾軒,早前才和其他學者出版了一份在他入獄前合寫的學術文章,題目為 Cooperate But Divided at Heart 。當中正提及不同路線、互相抗衡的人,可以在極權下互相合作。這也是馬嶽描述的「反抗的共同體」,是經過眾多社運事件交疊而成、具備情感力量的一群「人」。其實,中國共產黨時常高舉的「外國勢力」馬克思,他的《資本論》也認為,工人可以透過共同的被壓迫經歷(例如書中提到的「異化(Alienation)」)來團結成「反抗的共同體」,從而推翻權力階層。
但這就是國族嗎?讀者問的「人和」及所謂「立國想像」問題,其實道出這種以「痛苦的共同體」作為根基的困境。這恰恰反照在今天的「香港人」群體身上。
道理很簡單,「反抗共同體」只假設了這個世界有兩種「力量」,維護權力和反抗權力。因此把社會上的人,重新劃分為「好」與「壞」,「朋友」與「敵人」。而群體中只會想像「我地唔想要一個點樣嘅社會」,對於「我地到底係點樣」其實沒有作出太深入的討論和思考。因此,群體中很容易就會出現「敵人太強大,唯有打自己人」的情況。這句說話不是我發明的,是由一位流亡海外的媒體人告訴我。當時這位媒體人就是慨嘆,當出現分歧的時候,一些人就把反抗極權抑壓的情緒,倒灌在一些自己不同意的「自己人」身上,令群體出現互相拉扯的惡性循環。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1.0
試想想,「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是一種有效梳理分歧的方法嗎?不,這只是一種相對消極的暫緩應對方法。但這種消極的方法,卻能夠在街頭運動上帶來非常重要的啟蒙作用,就是清楚地告訴每一個抗爭者放低理念矛盾,要對準政權,然後憑著自己擅長的領域尋找崗位。
的確,2019 年的香港人透過許多不同的口號,在街頭上至少塑造出一種團結性。今天的政府和委任法官,針對「光復香港」的煽動性問題,也是在針對這種「聚眾」力量所作出的打壓。但不少人都會認同,現在香港人所面對的局面,是任何本地街頭抗爭都充滿代價,而血肉的痛苦、警暴畫面已成為歷史,隨之而來是日復一日的審判、抗爭者孤獨面對的收監,和一些沒有盡頭的流亡。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談「立國想像」?
其實,「痛苦」只能支撐「反抗的共同體」,難以建立具備國族性的「想像的共同體」。我自己的研究有部分是在反思,一齊「反極權」其實不等於共同擁抱「民主」,不等於擁有共同「文化」,也不等於共同產生對「開放」公民社會的想像。反過來說,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努力建立「香港人」的新定義。
就例如,九十年代的香港人,可以用「恐懼回歸」來形容;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的一年)的香港人,也許可以用「擁抱祖國」來形容;而過去十多年的「香港人」,則可以用「反抗與痛苦」來形容;至於今天與未來的香港人,「立國」實在遙遠,反而應該要思考「未來,我們想要一個甚麼樣的社會形態?」並以此形容我們的群體。
積極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2.0
這種「未來」想像不是要空想發夢「立國」、活在平行時空;或忘記過去,將現在受苦的人置之不理。反之,是我們如何透過現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行動和組織方式,尋找一種更高層次的未來社會基礎想像:一個社會一定不只有政治集會和國會工作,還有很多民間和文化的工作。今天的海外港人,確實就在舉辦不同的文化展覽、音樂會、食街、畫展、電影放映及宗教集會等。我們不應該要求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政治性」的行動綱領,而是應容許更多非政治性的活動,使其變成「香港人」的「軟實力」(Soft Power),一方面從群體內部凝聚更多參與者,另一面則對外輸出,抵抗外國把所有黃皮膚的香港人、臺灣人等,都當成 Chinese 的錯誤認知;第三方面,讓本地和海外港人看見在非政治行動上有共同參與的可能。例如海外港人飛回香港支持香港足球隊、音樂節,又可以有海外團體邀請在香港本地搞音樂、電影、藝術的人,到海外進行交流。
這種「積極的兄弟爬山」方式,不必刻意要求所有人都討論何謂立國想像,只需感興趣的人繼續努力討論、思考和尋求共識。而對一些不積極參與政治的流散港人來說,他們需要的是一種可以「落地」的生活信仰。因為實際上,「立國」是非常遙不可及且耗費心力的想像。因此,莫論跑道,今天的本地和海外港人,都應該要一同建立這種香港人的「信仰」模式。
二百幾年前,哲學家盧梭提出一個概念叫 「公民信仰(Civil Religion)」,在近代社會學發展出一個群體行動的概念,那就是人透過實踐(Practice)產生一種對道德和政治信念的共同性,從而建立群體的基礎。
這裡的意思是,「光復香港」作為一種信念,可以很遙遠,群體中可以對這想像有分歧和落差,難以達成共識。當然,不少人會認為,相關討論仍然需要持續,容讓不同的人知道彼此之間不同的理解和出發點;這也會是在光復一天,須要處理分歧的重要基礎。但對於更多的本地和海外香港人,「光復香港」不應只是一種口號式的信念,而是一種實踐的生活方式。
「感動的共同體」信仰
「今天我把這份工作介紹給你,不是因為我可以得到回報,或要求你做甚麼政治行動,而是我想讓你都知道,我們都是香港人。」這是近年我聽到最接近「公民信仰」的說話,就是要把很高深的政治信念,落地深耕,化在每一日的生活中。不必高調說出政治取態,但經歷的人會看見這種政治帶來的動力。
雖然時代很黑暗、世途險惡,有時就像填詞人黃偉文在盧廣仲《勵志論》所說「路見不平仆街」,一方面,幫了人卻被陷害,一起共事卻被出賣;另一方面,漫長的光復路上難免崎嶇不平會跌倒。但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可以選擇我們的人生。如果希望社會有天能改變,不論你思考的是怎麼樣的「光復」,我們都必須先要有一種生活形態的想像同實踐。
如果香港人曾經被 2019 年地鐵售票機上的「散紙、銀仔」感動,那麼我們當今的問題,不是要懷緬過去的美好,而是要看清今天仍在受壓迫的人和香港人在各地流散的處境,思考如何將這份「感動」延續並實踐下去。因此,就算今天「我」和「你」只是一起在修讀一個課程,好讓自己未來更容易找工作,但我們基於大家都是香港人,萍水相逢、定期食飯,在一起互相關心幾年後,建立到一份關係,這已經是在白色恐怖年代很難得的緣分。
一個社會,因為有人,才有希望。政治,因為有感動人心的「公民信仰」力量,才可以從艱深難明的行政操作和憲法原則,走入群體和生活的共同經歷。我們要繼續思考,如何在尚未立國(State)之先,就在生活中建立出一種「公民信仰」的民族性,還可以容讓我們的下一代,以及當地社會的其他人,經歷這些「感動」和加入我們,製造一種積極且遍布全球的「兄弟爬山」共同體意識。
所以,最簡單的回應,應該是不要介意所謂「Mass Population」沒有政治性的立國想像,反而要努力尋找維繫不同關係的方法,讓在做不同工作和崗位的香港人,在生活中繼續維繫我們透過「香港人身分」建立的「群體性」,假以時日,這些網絡就會產生翻天覆地的影響,組成更強大的「香港人」國族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