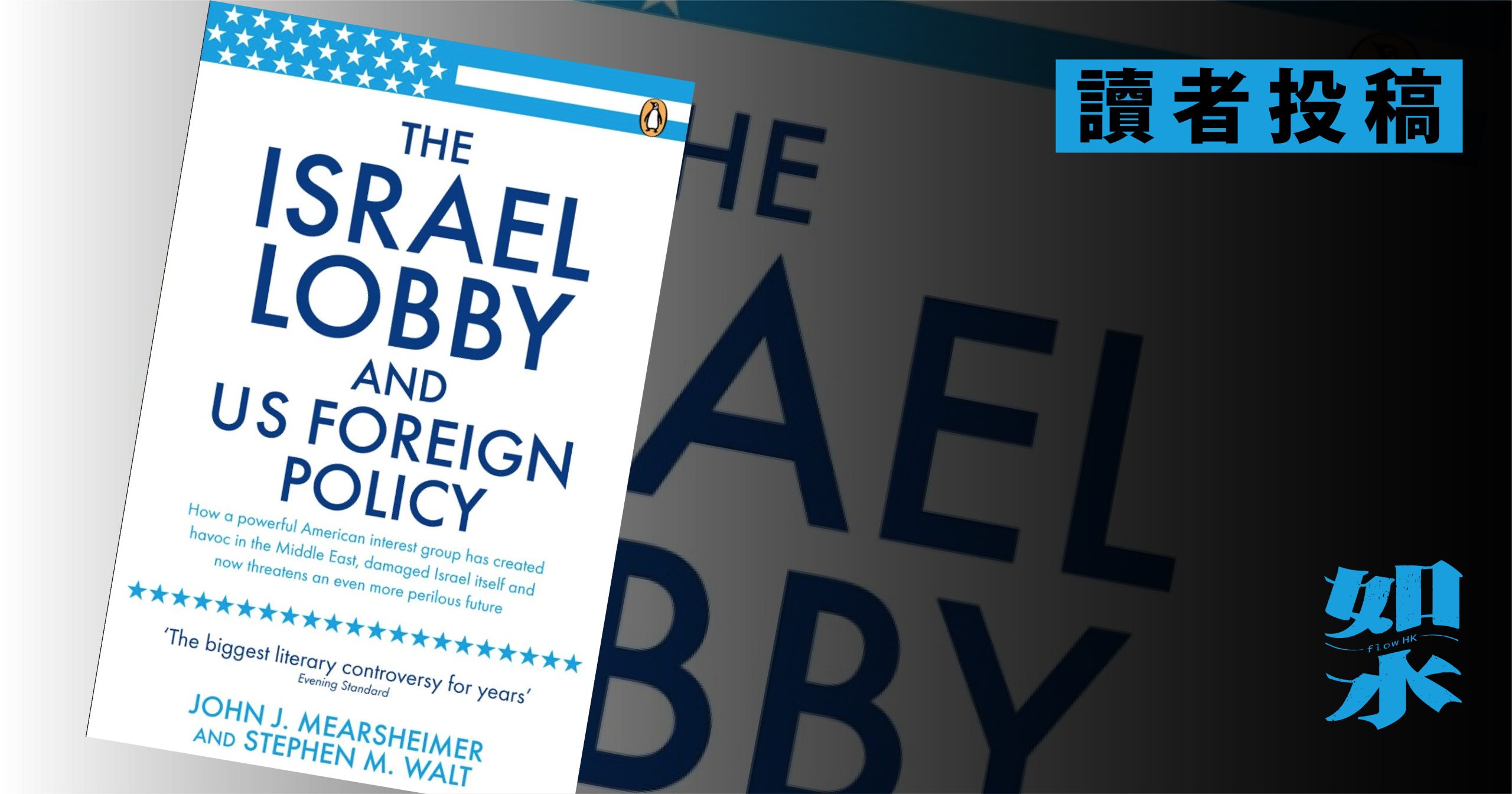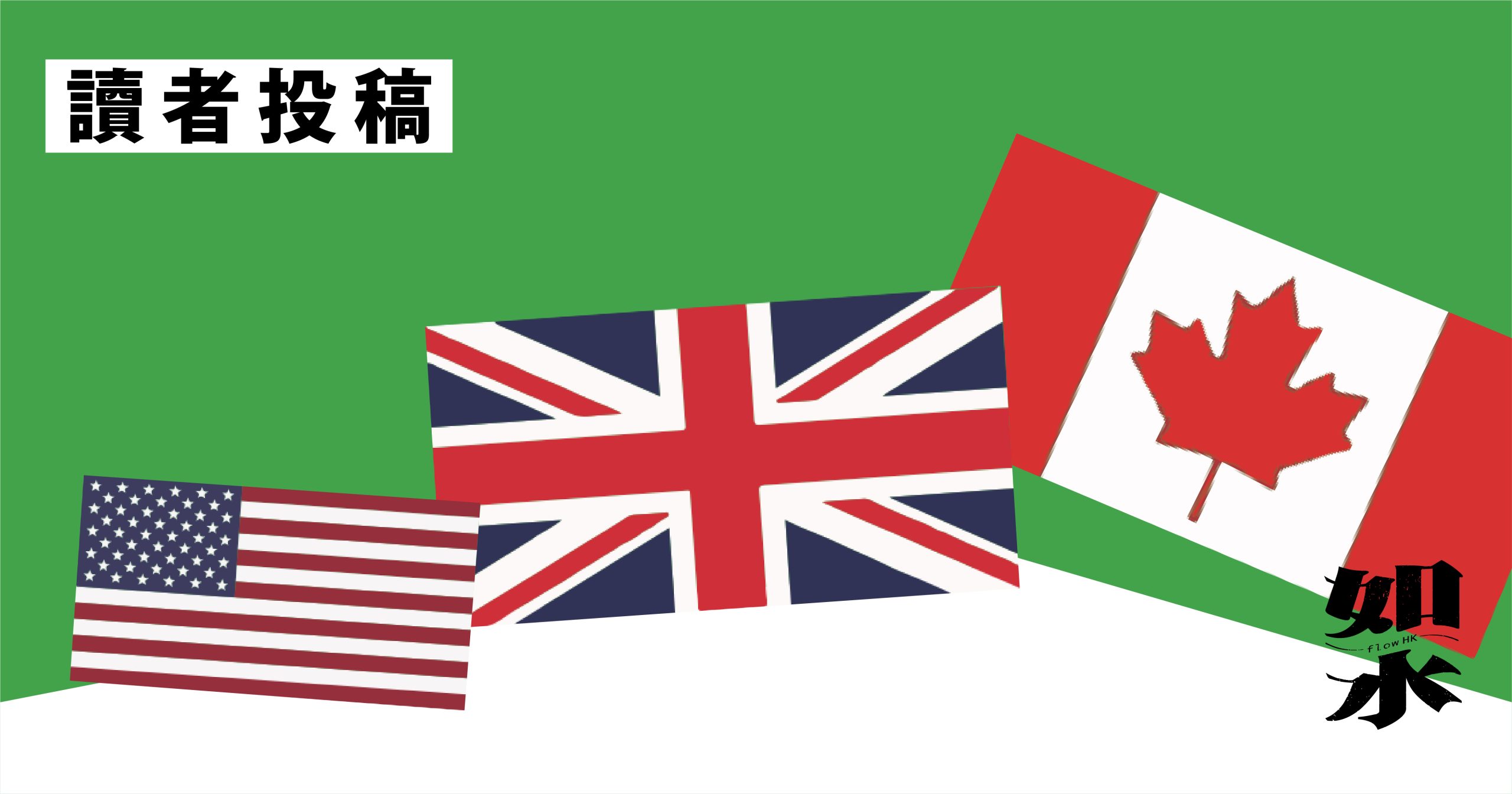MIRROR 粉絲的共同體與過渡空間——香港文化的社群面向

近年香港文化回潮,無論樂壇、電影、抑或「文青」崛起都使得香港人以不同形式投入當中、思考文化與共同體的意義,筆者不懂什麼艱深的文化理論,只明白香港文化不能沒有香港人,這幾年來文化所賦予香港人的特殊空間、所營塑的一種社群模式、所帶給香港人的成長很值得我們留意。
不知有否受近年抗爭的廣泛使用影響,現今流行文化似乎相當圍繞 Telegram 發生,幾乎大大小小的明星,從當紅的如林家謙、MIRROR,以至一些 KOL、model也有自己的粉絲群組,這些大大小小的社群在偶像文化、資訊傳達、粉絲交流中是重要的平台,重要到連早些時候 Anson Kong 退出群組也可成為一則娛樂新聞。
這些社群裏的話題林林總總,有分享今天午餐食物的,也有討論詩詞文學的,會動員當中的成員策劃一些「應援」活動,亦有不少是有利社會公益的,例如組織義工隊到動物服務機構提供協助、在疫情當中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物資「送暖」等。
這是相當罕見的現象,香港人從來不是以熱情、善於社交著稱,而可以用「摺」、內向來形容,這裡卻忽然出現自七十年代後失落的鄰舍/社會關係,當然這是一種共同體、時代精神的實踐,我們卻也從中開發了一種流行文化的功能與面向,就是提供一種「過渡空間(Transitional Space)」,轉化抗爭留下的能量,發展一種社群的新可能。
過渡空間是一個心理學概念,具體展現是不少人成長當中父母送的小熊公仔、模型車、玩具,使用這些物件會協助親子建立結連,物件也會在這些使用當中增添意義,筆者觀察現今香港流行文化亦擔當了這種功能,連結起各式各樣的香港人,譬如在這世代與階級矛盾的社會,身處基層的花樣少女與芳華正茂的有錢 auntie 便能因着姜濤走在一起,身為姜糖的他們平等地一起討論日常、分享各自感受、以偶像之名做各樣的事。
因着文化之名,香港慢慢發展出 「粉絲行動主義(Fan Activism)」,由為偶像著想開始,顧及討論群組的內容、其他人的感受,又因為思考怎樣塑造更好的粉絲形象而開始與社會互動,有機運用各自力量,動員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服務行動,同時建立、發展、推廣相應而成的社群倫理,例如近年對著歌手「鼓勵而非批評」、反對「私追」的態度也算是一種道德觀點的輸出,為香港文化提供正面的影響。
可這不只停留於流行文化層面,好像 Mirror 演唱會的內部認購議題便啓發了一些觀點,探討粉絲社群是否能夠改變演唱會的商業模式,讓商業行為更多由消費者主導,並且有更多回饋;當然在後來舞台裝置意外事件中,粉絲更扮演了關鍵角色,發表公開信譴責主辦機構,掀起的漣漪讓大眾反思舞者安全保障以及大公司商業道德。粉絲社群扮演了一種倡議角色,在經濟、倫理等不同層面為社會發掘、提供新選擇,當中的力量不容忽視。
當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正蹣跚學步,又碰上流散與政治低氣壓,流行文化便是一所溫室,好讓我們得以實踐社群生活與公民動員,並從社群生活習得身分認同帶來的責任與力量。探討甚麼是理想的社群模式、甚麼是成員應有的責任,正是共同體不能走的兩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