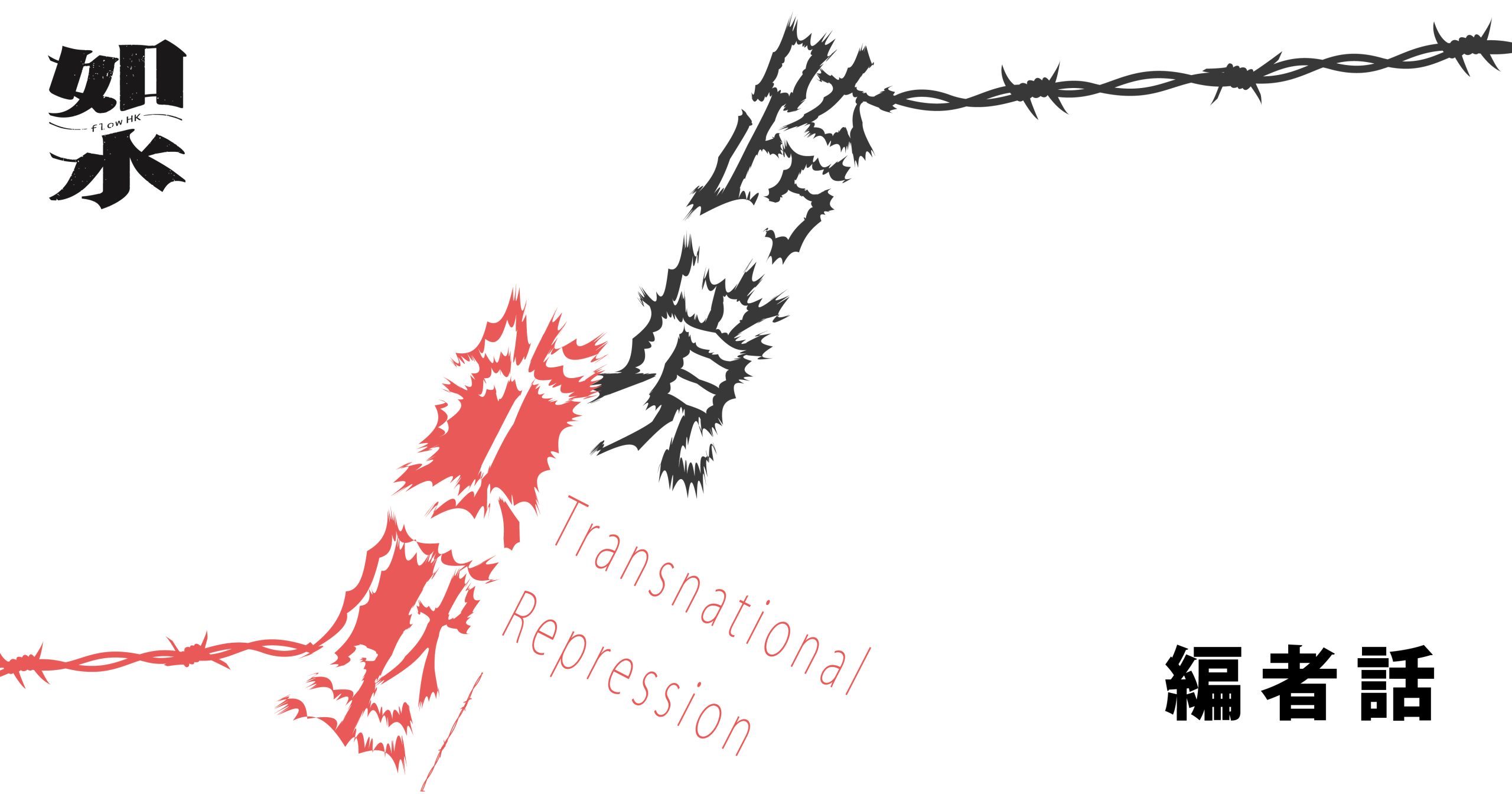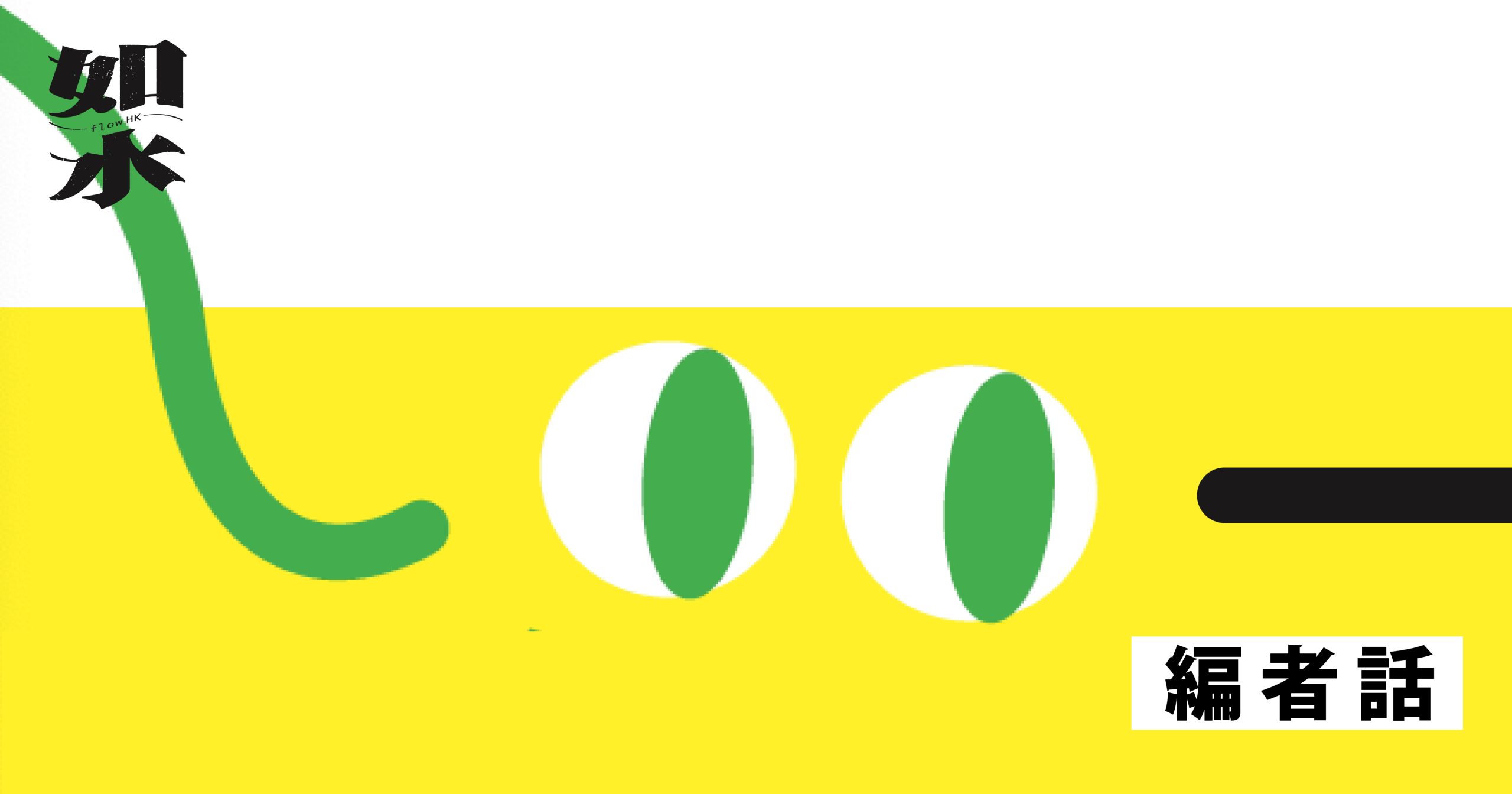海外抗衡「大外宣」 何以困難重重?
編者話:環球流散媒體與香港

今期《如水》談「流散媒體(Diasporic media)」。讀者可能會一頭霧水,到底甚麼是流散媒體?筆者向香港、臺灣的友人介紹時,就說到:「通俗而言,即是一些離開了原居地在海外運作,但仍然關心原居地社群的媒體,我們《如水》也是一例⋯⋯」
在國安法後,多間香港傳媒逐一停運,與此同時又有一些新的媒體誕生,面對這個現象,今期《如水》分別訪問《同文》、《棱角》兩間流散媒體,亦訪問了 RFA(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副主任胡力漢,一起探討現時在香港做新聞的環境,以及已在海外的流散媒體能做些甚麼。
RFA 是目前在香港仍有辦公室的外媒。在《國安法後 港媒噤聲 流散媒體資源弱 RFA 能做甚麼?》的專訪中,胡力漢自言:
「我覺得現在香港媒體有好多自我審查……不該說他們自我審查,而是大家都不清楚紅線在哪,所以香港媒體會退得好後 . . . (至於)香港傳媒可以做的,我們都可以做,而且還可以比香港媒體行前一步 . . . 面對(國安法)『紅線』,我們可以企得硬啲」。
雖說 RFA 可以相對「企得硬」,但在香港做新聞還是有不少局限,像是難找合適的人做訪問,他坦言在香港「基本上做唔到嘢」(當然,在海外做新聞也有一定的挑戰,下文會講述);還有一點,即使 RFA 相信在國安法下仍有辦法在港運作,但是否有美國政府資助就凡事都無所畏懼?答案是否定的,而令他們最擔心,是聲言即將立法的《基本法》第 23 條,會不會針對外媒。
「以我所知(若然立法後)有很多外國媒體都⋯⋯都咩嘅啦,都摺嘅啦、都走(苦笑),多間外媒都收縮得很厲害。」—— 胡力漢
當許多外媒離港,香港發放新聞的渠道減少,海外香港媒體就變得更有價值,筆者作為在流散媒體工作的一員,認為除了可以利用海外空間繼續為香港議題發聲,同時也在制衡政權外宣,讓外界聽到不同港人的聲音。故此,今期的主題訂為《流散媒體如何抗衡國家機器?》
在《訪問〈同文〉、〈棱角〉與香港民主女神:流散媒體如何在緊絀資源下生存?》的專訪中,他們不約而同講到在海外做港聞有一定局限,其中:
「海外的流散媒體無法如香港傳媒一樣快速、在現場報道即時情況,亦要依賴香港傳媒的第一手報道。」——《同文》總編 YC
「畢竟人在海外,能取得的新聞資料已是第二、三手,但相信仍可做到一些香港傳媒受國安法『紅線』所限而無法選取的新聞角度。」——《棱角》總編輯 Jane Poon
除此以外,流散媒體大多面臨資源短缺的問題,因為難像主流媒體般有持續、穩定的廣告收入,只能靠讀者付費訂閱,兩人皆說因此裁減人手,其中 Jane 說,希望減省支出能更容易達到收支平衡:
「無辦法啦,(目前)只有 cut(人手)啦⋯⋯大家同事都明白 . . . 因為大家都想做到落去。」
破曉的評論文章《遙控器上的香港:比起媒體,未來更需要的選擇是……》就不看好香港流散媒體的前景:
「歷史軌跡表明,離散媒體成長所依賴的翻譯外電和移民專題,需求將隨後代融入當地社會而下降。有心人成功配對資金支持仍要面對缺乏影響力的困局,畢竟目前的復甦假象掩飾不了市場萎縮的事實。雖然多間新辦媒體先後吸納以往具公信力媒體的班底,但整體影響力疊加起來,仍不足以彌補一間傳統媒體的消失。要麼只能專注一類新聞、要麼隔周刊登深度報道、要麼在多地頻密更新而分身不暇。最不方便的真相是,即使媒體數量反彈,留下來的人發現以碎片化網誌的方式苟延殘喘,已難以重奪流失至綜合性外媒和專門時事評論的讀者群。」
然而,面對財政壓力、讀者群流失致難以經營下去的,不只是流散媒體,同樣在國安法後成立,但紮根香港的新媒體亦然。Channel C HK 今年 6 月初「告急」,指一直以來大力支持該平台營運的「有心人」無法繼續提供財力支援,Channel C HK 須在一個月內自負盈虧,否則將在 7 月12 日開台兩週年之際停運。港人聞訊後一呼百應訂閱支持。
《同文》總編 YC 在訪問中提到:
「有賴《蘋果》當年推出訂閱制,讓港人慢慢接受付費閱讀,現在大家都比較願意捐錢給與民主自由有關的組織及媒體 . . . 《同文》今年有開設 Patreon 接受公眾捐款,儘管收到的款項不算多,但至少可以補貼一部分支出。」
那麼有多少香港人願意「課金」支持香港媒體?今期《如水》製作的 infographic 《海外、居港港人 有幾信任、支持香港媒體?》,希望與讀者、傳媒行家一起探討這個議題。我們在《如水》各個社交媒體發帖,邀請公眾分享對於香港媒體(包含國安法前、後成立之海外及香港傳媒)的可信度,以及每月願意花費多少錢訂閱等資訊。
我們透過數據發現,不論在香港還是海外的受訪者,無「課金」者皆超過四成;而願意每月付費者當中,分別有 57% 及 75% 人報稱每月支付金額為港幣 99 元以內。不過,居港受訪者相對比海外受訪者更願意支付較高金額支持傳媒機構,前者有約 25% 每月支付超過 100 港元,而後者僅 14%。
至於哪間傳媒在受訪者心中可信度最高,容筆者賣關子,請讀者在今期《如水》中找答案。
在我們這本 160 頁的雜誌裡面,當然不只是訪問傳媒行家,還有其他持分者。筆者在本期雜誌撰寫《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仍在海外讀新聞?》的報道,訪問了在 2019 年反送中後,赴英國、美國及臺灣讀傳播學系學士及碩士課程的香港學生,以瞭解他們為何明知香港新聞機構萎縮、就業機會減少,加上香港新聞自由度大幅倒退,仍繼續讀新聞相關科系。
筆者發現,他們或多或少是受到反送中事件影響,但不一定是受抗爭運動啟發而想做新聞,就如在美國讀大學的 Ariel(化名)就談到:
「因為(在旁聽的過程中)法庭內不可拍照或錄影,只能靠文字記錄,我希望自己未來能用記者的身分,透過報道記錄這些歷史,『否則可能之後就無人知道入面發生過甚麼事』。」
其實,她大學主修地質學,正是因為反送中,才突然副修新聞系,及後還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副修科目及做該校學生報記者,對此的熱誠更超越主修科系。
在英國讀書的 Reagan 想做記者,是源自從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加上讀中學時讀到《傳真社》的一篇報道,讓他認為記者追查鮮為人知的事件讓公眾知道,「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職業」。
至於在臺灣攻讀傳播學院碩士的 Patty(化名),是本篇 3 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人在香港讀過新聞系,並曾在反送中前線做採訪。會去臺灣進修,她不諱言其一原因是不想留在香港發展,也不想在香港繼續讀新聞。從筆者與她交談,察覺她對新聞行業前景的看法較另外兩位悲觀,對未來會否從事新聞行業,她的答覆也比較模稜兩可:
她認為,臺灣傳媒薪酬待遇較差,行業前景不太明朗。她亦會考量做傳媒能否幫助她未來的生涯規劃 . . . 她坦言不想在臺灣做即時新聞,只想做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 . . . 若找不到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則可能考慮做 Marketing 或者於研究中心任職。
而在訪問中,他們均告訴筆者,在學業或學生報上,做過、或爭取過做有關香港的議題,但當筆者問及假設未來在海外做傳媒,會否想繼續做香港議題,三者均認為該 move on,其中 Reagan 指出,2019 年香港反送中驅使他想做記者,只是一個起點:
「我不單只做香港新聞,甚麼地方的新聞我都想做。再者,做香港新聞,受眾真的太少了,我希望用英文做新聞能夠擴大受眾,為更多勢弱言輕者發聲。」
講到語言帶來的制肘,目前香港的流散媒體主要都是以中文發稿,這會否局限了傳播範圍僅在華語圈子,難以「衝出國際」呢?是否該改變模式要出雙語報道?
我們編輯部同事 Jacky 在《專訪媒體及傳播學者 Yazan Badran 流亡新聞的複雜性:敘利亞媒體對香港記者的啟示》一稿,訪問到專注中東和北非地區新聞和政治活動、研究敘利亞流亡記者的學者 Yazan Badran,他以敘利亞的經驗指:
「這對敘利亞媒體來說已經成為必要,現時大多數敘利亞媒體都是以雙語出版,至少有部分報道是這樣處理 . . . 對香港而言,首先,我想中國大陸如此龐大、資金充足,而且有國家支持,香港媒體不可能通過出版中文雜誌帶來甚麼變化。
但我認為,在另一方面,即使香港媒體只在一定程度上主動與華語圈的其他讀者互動,香港媒體也有一個基本責任參與這個更廣的公共領域 . . . 因為一旦你開始翻譯,你就開始在一個不同語言的語法及思考邏輯中重新思考問題,並試圖把它們翻譯成一個不同的範式,同時在該翻譯語言的文化領域生產知識。」
今期《如水》的兩篇學者訪問,英文版會在網站上刊出。
然而,流散媒體並非香港、敘利亞獨有,全球各地只要有極權的地方,就會有流散或流亡媒體出現,有些甚至已有幾十年歷史。
就像今期《如水》獲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授權,將流亡海外的著名新聞網站 Confidencial 的編輯、尼加拉瓜記者卡洛斯・F・查莫洛(Carlos F. Chamorro),今年在《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內容翻譯成中文發表。
查莫洛的身世頗為特別,其父生前是《新聞報(La Prensa)》總編(1978 年遭暗殺),查莫洛就在一個月後、獨裁統治下展開其新聞工作生涯;至於其母親,1990 至 1997 年間曾任該國總統,推動民主轉型,不過,隨著現在的當權者奧蒂嘉(Daniel Ortega)自 2007 年重新掌權以來,當地的民主體制就大幅倒退,甚至加強管控媒體:
(政權)設計出一套傳播戰略,強制推出所謂「未受污染資訊」,也就是她所謂的「純淨狀態」的資訊,通過官方媒體直接傳達到市民手中,不經任何獨立媒體的質疑或調查。
這種專制政府的模式,在 2018 年 4 月爆發的公民抗議運動下崩潰,政權看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遂以殘酷的鎮壓作為回應 . . . 並視新聞界為要粉碎的敵人 . . . 2020 年,政府通過「網絡犯罪特別法」,針對透過社交媒體和媒體機構傳播的所謂「假新聞」,並將涉案者處以 1 至 5 年的監禁。
何謂「假新聞」?當局無定義,某程度上是政府說了算。查莫洛說到,在法例生效後,至少有 20 人因而鋃鐺入獄,包括記者、社運人士、牧師,甚至一個沒有任何社交媒體賬戶的農民。他的 Confidencial 編輯部,則分別在 2018、2021年兩度遭警方查封,迫使他們流亡海外,在異地繼續無間斷做原居地的新聞。
另外,Confidencial 還是今年 4 月在意大利佩魯賈舉辦的國際新聞節中,題為「流亡媒體不只是潮流(Exiled Media is Not Just a Trend)」的講者之一。《如水》編輯部一篇《佩魯賈國際新聞節 流亡媒體網絡 NEMO 正式成立》,記者專程前往意大利,參加及報道這場歐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傳媒業界盛事。在這場討論環節,5 名分別來自緬甸、尼加拉瓜、俄羅斯等國家的媒體機構,其流亡媒體人進行小組討論,當中談及營運財政壓力,還討論到流亡媒體的目標受眾群:即應該面向(原居地的)本地居民,還是已經流散到海外的流散社群?
如果選擇以流散社群為主要對象,傳媒機構便可能須要面對流散族群人數遠少於本地居民的現實。讀者人數不足會導致影響力不足、資源不足,傳媒工作可能會難以持續。儘管如此,放棄流散社群讀者、專注於本地讀者也未必是出路。最明顯的問題是,媒體工作者如何在異地報道自己家鄉的事。在拉脫維亞報道俄羅斯新聞的 Medusa 總編輯及創辦人之一 Ivan Kolpakov 坦言,「每個流亡媒體都會努力為他們的母國提供服務,並期望自己能與本地民眾保持聯繫」,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對於流亡媒體來說仍是個挑戰。
那麼,這些問題究竟可以如何解決?顯然沒有標準答案。事實上,即使有,答案也可能隨著時局的發展而改變,例如新科技的出現,可能會帶來新的解決方案,但威權政府採取新的打壓手段,又可能會加大應對問題的難度。——《如水》編輯部 著
也就如標題所示,5 人藉該活動,正式宣布成立環球流亡媒體網絡 NEMO(Network of Exiled Media Outlets),希望能將全球的流亡媒體連結起來,讓彼此能夠互相幫助、互相借鏡,以令流亡媒體工作者能夠一起走過艱難的路。
《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則寄語:
「尼加拉瓜的經驗表明,在獨裁統治下,流亡新聞業的抵抗並不足以為民主變革鋪路,但只要他們保持信念,繼續做更多、更好的新聞,新聞自由的火焰就會繼續燃燒,成為所有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
上文有提及到,俄羅斯也是一個有不少流散海外媒體的國家。凌志豪撰寫的《風暴中的獨立之聲:流亡中的俄羅斯地區獨立學生媒體》,訪問了網上學生媒體《風暴(Groza)》創辦人 Marina Bezmaternykh。受訪者已在俄烏戰爭後流亡海外,而她的媒體在經營 3 年後,正打算轉型。
轉型有兩種,一種像是《同文》,避免各家海外香港媒體都做一樣的事而力量抵銷,所以按實際情況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尋求改變。另一種就如俄羅斯的《風暴》,原是關注當地大學教育議題,現在因為當地政局愈趨敗壞,故想轉型成一個推動公民教育的組織。Marina 指: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年輕人急需學會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 . . . 例如由(學校)宿舍問題到(俄烏戰爭)軍方動員入伍等生死攸關的課題,人們需要知道如何自保 . . . 在現時的俄羅斯談人權是極為矛盾,儘管法律明文賦予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人權的狀況亦是如此。」
像這種的做法,香港亦有類似。香港民主女神的「本業」是聚焦在藝術及文化方面,加上團隊成員皆非做/讀傳媒出身,據香港民主女神發起人 Alex 說,是「(藉此)提供平台為港人帶來不同角度觀察社會議題」。
對於媒體應否參與社會運動,在《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透明無隱:致力於社會運動報道的公正性》中,Terje S. Skjerdal 說道:
「如果媒體的主要動機是宣揚特定政治議題或代表特定政治立場,那麼我認為媒體需要公開這一點。他們需要保持透明,盡量不隱藏自己的意圖 . . . 其次,對於純粹的社運媒體,如果它唯一的動機是帶來改變、干預或推動某些政治議題,我對能否稱之為專業新聞有所保留。在這種情況下,它是與傳統新聞學所定義的新聞不同的東西。雖然,在當地社會完全滅聲,當局粗暴打壓言論自由和任何異見的情況下,我可以理解這種做法。」
Yazan Badran 也認同立場要公開透明,他以香港的情況表示:
「只要記者立場是透明的,我更願意閱讀一篇由一位記者清楚、透明地告訴我,他支持香港獨立運動,但更多層次、更深入的文章,而非一篇由外國空降當地記者寫的無味文章,因為外國記者去了那裡,也只會看到表面。與此同時,我亦可以閱讀另一位記者的文章,他可以告訴我他反對香港獨立 ,但為我提供更豐富和更詳細的細節。」
至於 Kennedy Wong 的書評《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評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回顧了香港的媒體歷史,講起新聞自由是「曾經沒有」,亦不是天長地久,「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還指在極權下,「沒有新聞是一種壞新聞 (No news is a kind of bad news)。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本地傳媒因國安法而噤聲,Kennedy 則相信,在海外的媒體有一定空間運作:
「例如《光傳媒》、《棱角》、《綠豆》等,其實依然會對本地和海外香港人社群產生影響。當香港網絡依然流動,大陸防火牆尚未來臨之前,這些新聞消息和討論,仍會成為連結海外與本地港人的重要聯繫。因此,一天尚有報道香港的新聞,而非『宣傳』香港的『新聞』,這便是一則好新聞。」
既然今期的題目有講到「抗衡國家機器」,《如水》重點文章是精心製作了調查報道《統戰部借香港秘密持〈歐洲時報〉大外宣 曾與〈經濟學人〉等知名外媒合作 英政府落廣告》。我們過去數月透過於英、法兩地實地採訪,以及查閱香港、法國、英國及德國的商業登記資料,調查號稱全歐洲最大華文媒體《歐洲時報》的架構與運作,並發現它實際上是由中共統戰部,透過一家香港註冊、名為「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的公司操控,公司成立年分甚至能追溯到 1980 年。
對此,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葉飛立(Filip Jirouš)接受《如水》訪問時表示:
「香港這麼多年來,尤其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之後,都一直被國家企業和機構用作進軍海外的渠道 . . . 這種做法令到西方政府更難看清這些公司的真面目,因為香港在商業與投資領域,一直被視為合法而且管治優良的地方。」
他又提到,中共操控海外傳媒影響歐洲輿論的手法已符合歐盟「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的定義:
「既然歐盟已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競爭對手,而且中國試圖干預環球民主國家政治的意圖愈來愈明顯,我認為合理的做法是審查相關機構,特別是接受外國資助的一群。」
筆者作為有分參與這個調查報道的一員,我們從蒐集資料、查冊、整理資料、實地調查及聯絡各方做訪問等,確實花了很長的時間、人力及資源(真是砸重金做調查);但在花心思做這個調查報道的同時,我們還是要處理其他稿件,有一段時間忙得天昏地暗(笑)。
趁著撰寫《編者話》,筆者懇請讀者們繼續購買《如水》雜誌、大力 CLS 支持我們的工作,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做深度報道;倘若這個調查報道的成果反應熱烈,編輯部會希望未來作進一步調查,但前提是需要得到大家實質支持。
借讀者莫離投稿《守望麥田:當代香港媒體的探索與挑戰》的一段話作結:
想起蔡元培先生一句話,「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筆者斗膽改幾筆,「要有良好的媒體,必先有良好的社會,要有良好的社會,就要先有良好的個人。」媒體固然匯聚、輸出文化,可羊毛出自羊身上 . . . 在演算法當道的時代,媒體的內容水平也是我們想看的內容水平, 媒體不再只是報紙、編輯的責任,自我、群體成長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