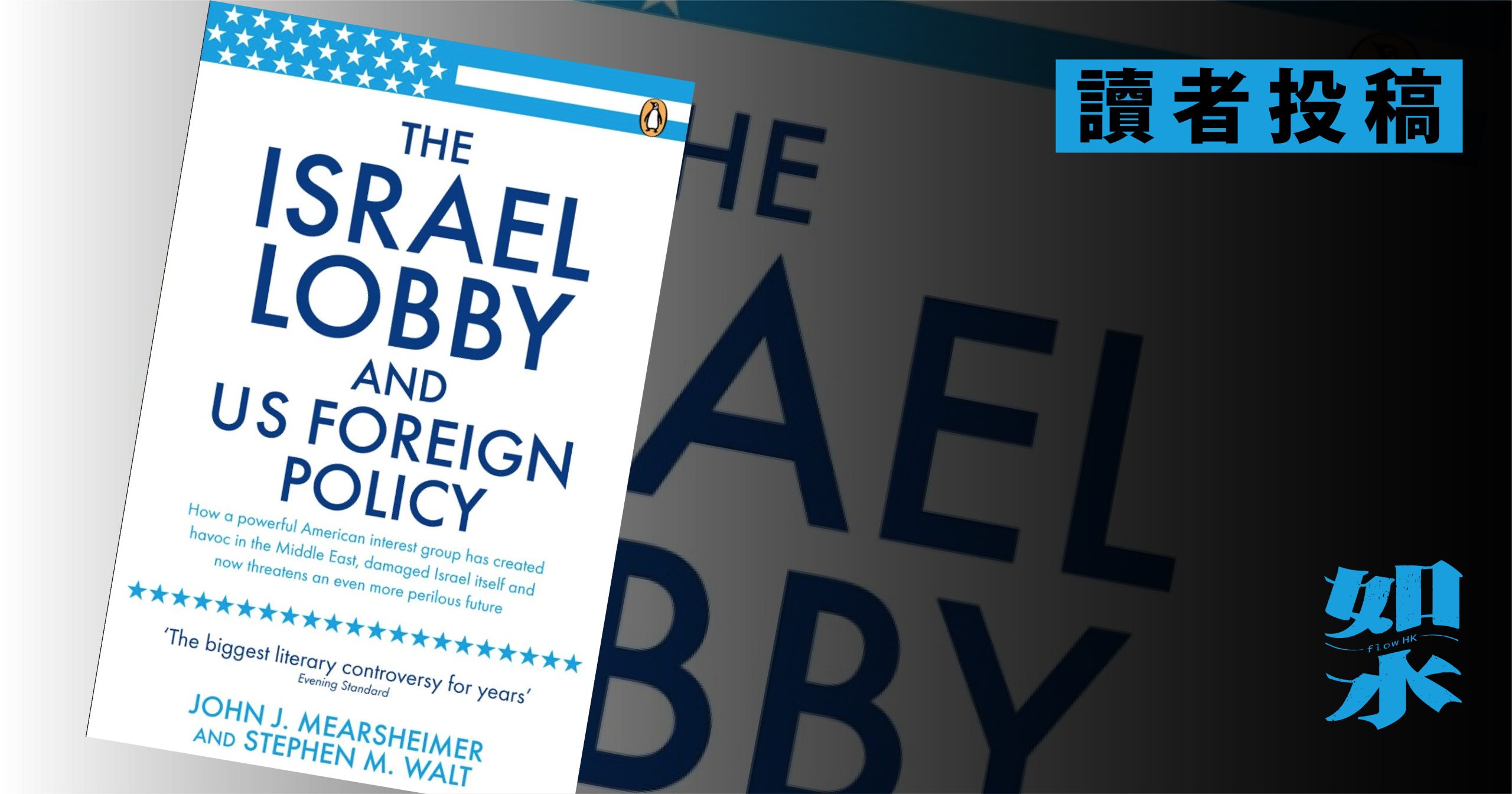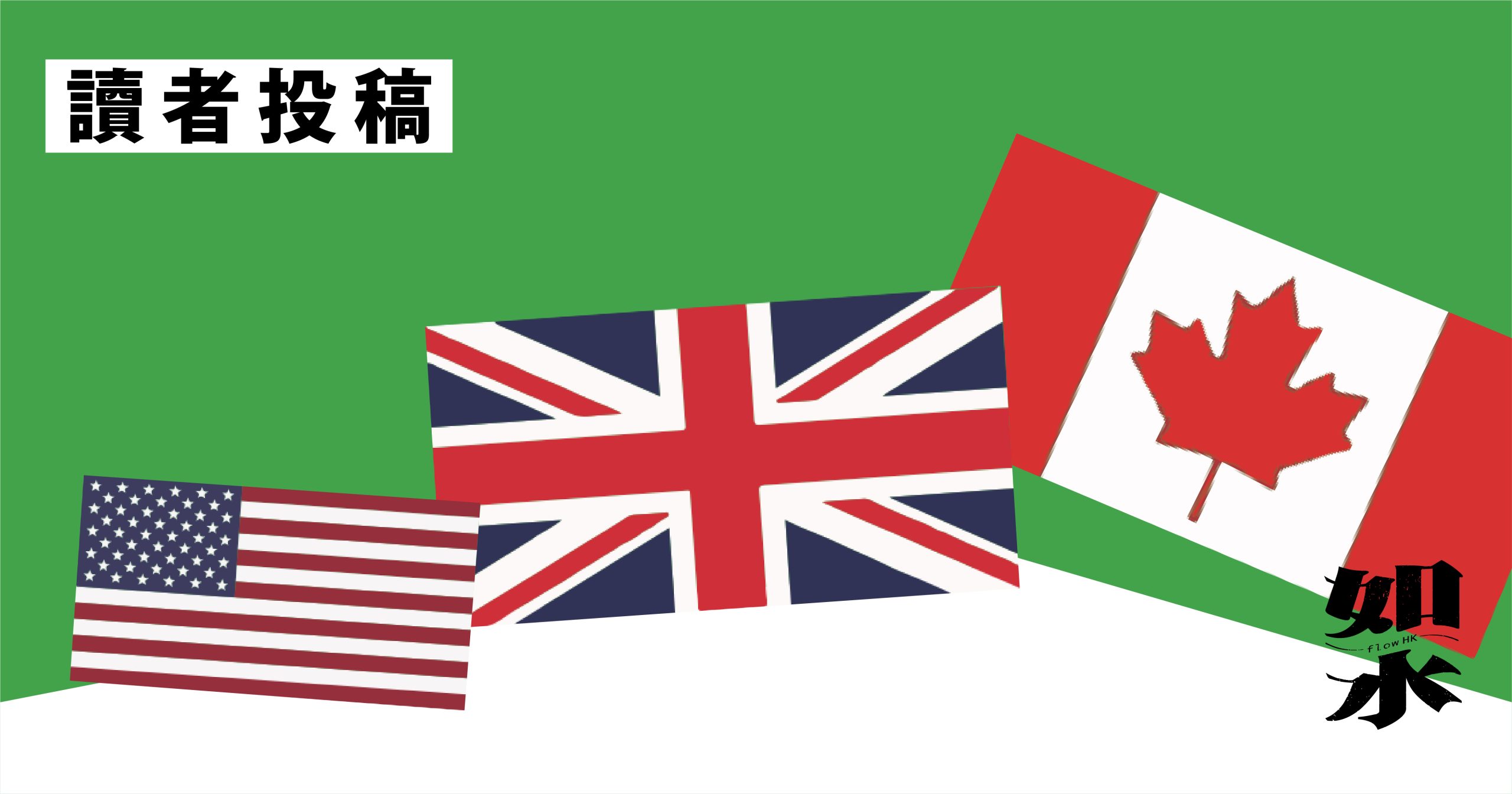——為經濟建立韌性與自主
自救與自保

若要選當今香港最搬得上檯面的自由,那必須是長年高居國際最前列的經濟自由;若要為香港民族的自由中,選一項最不能欠缺的自由,那則必須是香港人飯碗的自由。就算批評我短視功利也要這樣說,起碼它最低限度保障了選擇與不選擇的自由,也為知識的累積與價值的實踐提供基礎。如果民族不能有經濟的自主、取得民族的「財富自由」,那麼做甚麼也會是似被刀架著頸項,理想也會變成空想。
當年香港可是單憑一己之力擊退索羅斯的頂級財政體系,可是,此刻的現實就是經濟下行、物價上漲、福利無能,港共當政與民為敵,從上而下以一個又接一個的大白象工程,蛆蟲般揮霍香港庫房,令香港失去財政自主,人口被全方位、全階層清洗與入侵,「聽話」又低廉的「人才」搶去許多原本屬於香港人的工作崗位,無論是中環金融姐姐還是東涌倉務哥哥也人心惶惶,生怕明天一睜眼便失去工作。
香港面對一系列的憂患,海外港人尚未建立一個健全的經濟圈,莫論將海外資源導回故土長遠支持民族自主運動,即便是有一天中共倒台,所謂「支爆」實現,香港與香港人也必須面對最現實的問題——經濟不景與資源匱乏。若香港人彼時整體經濟負擔重、政府庫房空虛,同時經濟、社會、市民重度依賴政府資源/福利運作的話就糟糕了,財不能自主便是政不能自主,家與國也休想迎來自主的一日,最壞情況分分鐘是個無政府亂局,當不少人還是靠政府救濟金過活,社會何來保持基本經濟運作,民族何來自救自保?
想起有次問家母,貧瘠但政府干預接近零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個怎樣的地方,那時的窮苦大眾、尤其是住在「三不管」的九龍城寨的前輩是如何生存。她提起以前十幾個街坊聚在一起便可以組一個「標會」,為彼此提供短期貸款、在經濟上扶持對方,她談著談著也講起很多鄰里互相照應、幫襯街坊商戶、賒這賒那、送東送西的故事。當然,那是段艱辛、困苦的日子,可從前香港人便是這樣靠著民間互助、合作、扶持,在政府隱形、無福利、無管理的那段時間裡自強不息。政府無從干預市民的荷包,變相保障了香港市場自由,也為七十年代經濟神話鋪平了跑道,打下自立自主的基礎。
我堅信在當今的本地和海外香港社群中,這種民間互助的精神實踐尤其重要。中共管治機器鼓吹分化、篤灰,令人與人的關係疏離,固然使我們依賴政府生存和思考,但現代社會科技發展,亦使我們忘記社群生活的存在。我們向銀行借貸、向谷歌求助、與鄰舍關係疏遠,生活當中值得信任的關係寥寥可數;同時,所謂的組織、有豐富社會網絡的人也被政府收編統戰,於是所有資源、關係便落入極權與既得利益者手中,無依無靠的我們最終也必須更依賴政府了。
我們必須在最基層處建立屬於自己的民間關係與互助網絡,不得假手他人。我們需要一個自主、有韌力的民族與公民社會來對抗極權的滲透,也要靠它來支撐民主自由的發展。為此,在社會當中建立信任關係非常重要,而經濟上的互助是最直接有效的實踐,無論是為彼此提供福利、推介工作;光顧本地小商家和實業;以及資助有需要學生攻讀大學,也能使彼此有更多接觸、建設信任,為社群與民族賦權,在經濟層面減少對港共與既得利益集團(包括銀行、財團)的依賴,讓人、關係、本地產業成為經濟的主角,進而由此在政治層面減少依賴,削弱港共的認受性。民間緊密結合的關係網亦可增加極權鼓動分化篤灰的成本。有效的社群關係與經濟保護網,更能在混亂時維持基本的社會經濟運作,做到最基本的自救自保,甚至在有天港共敗走、百廢待興之時,減低新政府的負擔。
有時,與其糾結於中國崩潰與否,或香港宏觀經濟的問題,不如嘗試從民間層面的經濟面向開始未雨綢繆,確保香港也能在政府以外自主運作,自己香港自己救。香港的獨立不只是政治的獨立,也是經濟的獨立、產業的獨立、民族與公民社會的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