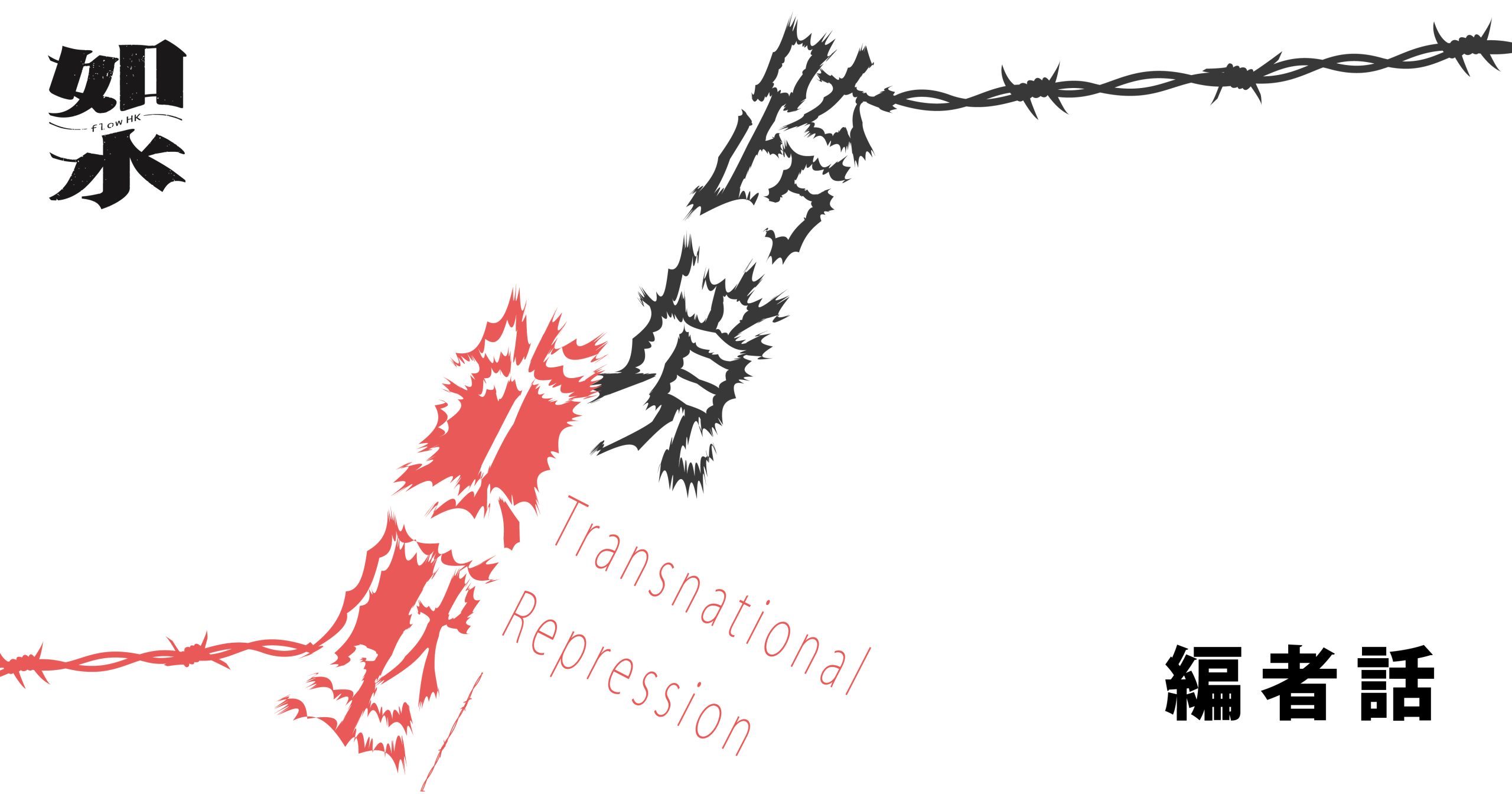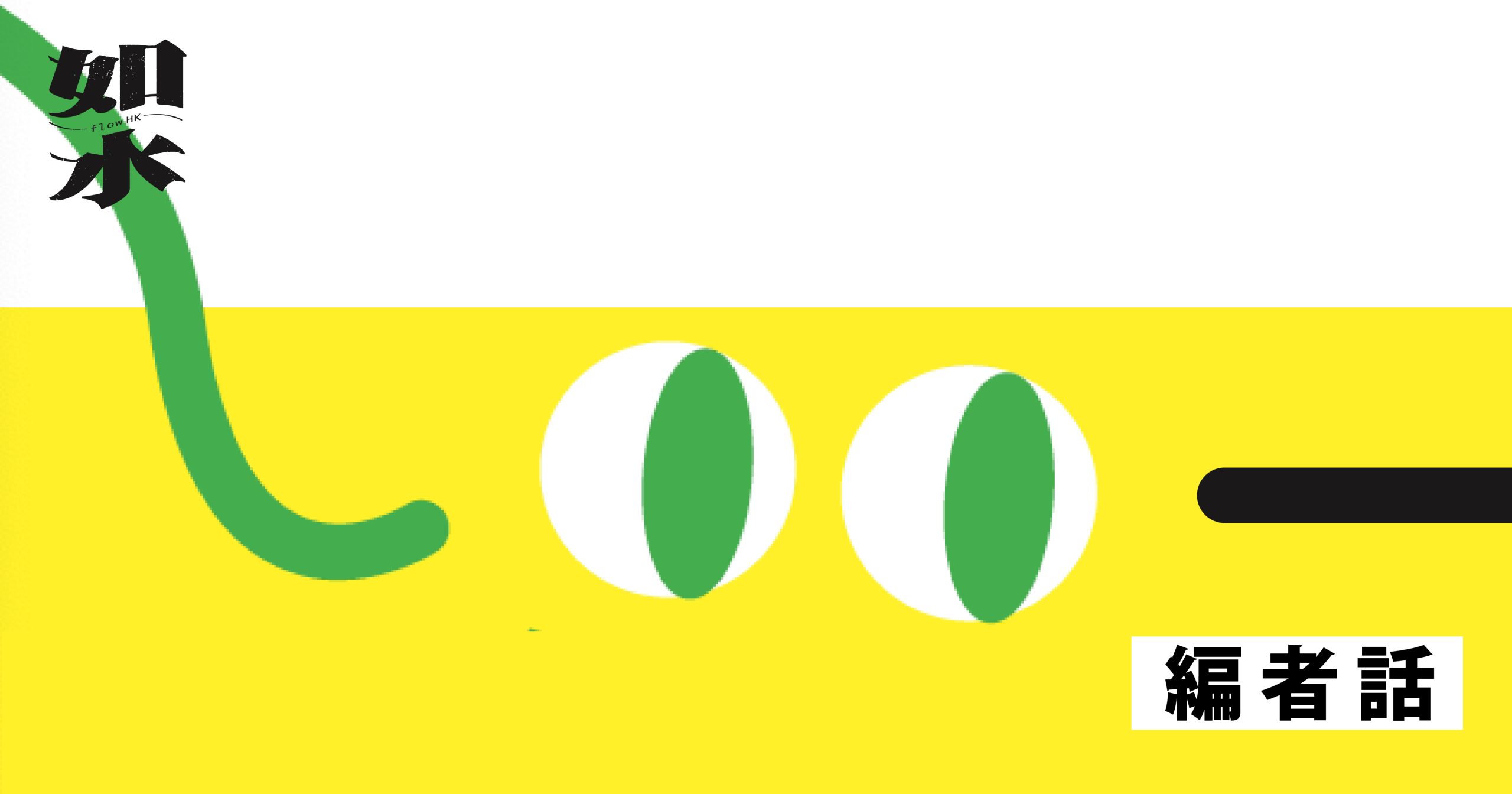流散社群能為香港文做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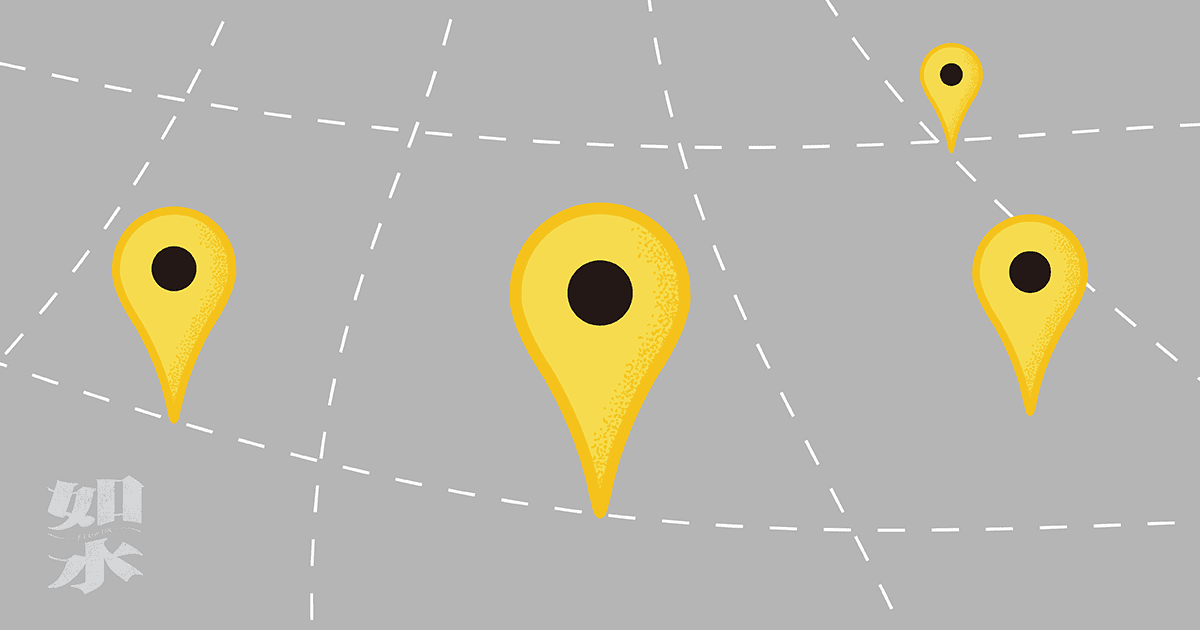
今期《如水》談「香港文化」。按道理這個題目已講到口水乾,雖說文化總是不斷變化,每日都有新話題可講,可有沒有必要用一整期超過一百三十頁的季刊,去講這個實在不算新的話題?你可能會這樣問。
有。這是我的答案。因為《如水》是流散港人的雜誌,而「流散時代的香港文化」,絕對是必須談論卻鮮有觸及的話題。
必須談論,因為我們看見許多新現象。論電影,英、美、澳、加,多部本土作品巡迴上映,叫好叫座,部分城市如倫敦甚至出現搶飛潮。論音樂,「鏡粉」活動範圍打從一開始就已不限本土,一群加拿大姜糖還以偶像之名跑去拉飛機(一部波音 757)為慈善機構籌款。為了食好味嘅半肥瘦叉燒,海外港人學會用彎曲的鐵衣架吊起豬肉放入西方廚房必備的焗爐。當然還有仍然好賣的文宣紀念品,和那些寫有「香港」或「加油」的襟章布章鎖匙扣。這些都是文化,而且是一種移民潮後頗為嶄新的現象。
我們可以怎樣談論它?自香港民族論興起以來已愈來愈為港人熟悉的 Benedict Anderson 會說,世界各地的流散香港人就是以這些文化事物,來想像自己是個共同體。這是我們早就知道的事,所以我不打算從這裡開始。
我想逆向聊聊,想像的共同體怎樣影響我們看待文化事物。
我們可以從今期冬甩撰寫的報道文章《給牆內的人寫一封信﹕香港流行文化於寫信師與筆友間》窺見這種現象。文章訪問了三位身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寫信師」。他們談到自己寫信的動機和內容。由於政治話題會被攔截,所以很多人寫的不是音樂就是電影——文化產物。作者精緻地將歌詞入文,讓人讀出只有熟悉廣東歌的港人才會明白的情懷,不過令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卻是,當許多人以為「寫信」這種行為是單向地幫助牆內人解憂解悶,文章提到寫信師自己,其實也在過程中得到療癒。
名叫「版主」的寫信師說﹕
「寫信是少數海外實際可以做的事,令我同香港繼續保持連繁,不會對香港有太離地的感覺。這些情感上的連繫很重要。我希望透過書信、文字與筆友保持溝通,分享不同想法,令他們知道我沒有放下他們,這些東西,也令我鞏固香港人的身分。」
另一名寫信師「大眼仔」亦指﹕
「在海外有空時,我會想繼續做一些為香港的事,寫信令我有仍然同香港人聯繫的感覺。. . . 除咗寫信,可以為香港做的不多,如果唔寫,就會覺得自己口講話好關心香港,但無實質去做什麼,會有一份內疚感,好過意唔去。」
上述兩段話反映了許多海外港人共通的心靈需求﹕繼續與香港保持聯繫、繼續強調自己的香港人身分。
這種需求之大,足夠推動電影市場。黃浩然的《緣路山旮旯》、陳詠燊的《飯戲攻心》,都在流散港人聚居的國家、城市接連放映,也就別說那許許多多的抗爭紀錄片,《憂鬱之島》、《時代革命》、《因為愛所以革命》……白瞄文章《移民潮下,港片會有海外生機嗎?》談到這一波(海外的)本土電影熱潮時,將之拿來與五、六十年代比較,指出當時《梁山伯與祝英台》、《貂蟬》、《紅樓夢》等邵氏電影以「文化中國」作招徠,「不只在香港成功,台灣也有大量觀眾,海外(東南亞、歐洲、北美等地)離散華人社群也甘之如飴」。箇中原因如下﹕
由於戰爭、各種的社會動盪和其他經濟原因,自上上世紀末至上世紀初,不少人從中國大陸出走到世界各地生活,有些人落地生根,但也有些人懷想故國,於是乎對有「中國味」的出品趨之若鶩,造就了邵氏(以及總體的香港電影)之海外市場,而這海外市場,一直支撐着邵氏至八十年代中為止。
白瞄說得對,懷想故國無疑是這些電影有市場的原因之一。不過我還推敲有另一理由﹕上世紀中沒有互聯網、華人相對教育程度亦較低。以英國為例,許多移民不諳英語,加上一心抱著日做夜做光宗耀祖的心態,生活圈子可謂自成一角,鮮有與當地社群交流。他們不會接觸當地媒體,不會去當地超級市場購物,不會去西餐廳吃飯,甚至連剪髮,都是幫襯「自己人」。如今成為旅遊景點的唐人街便是由此誕生。在這意義下,港產片和港產劇集(曾幾何時租 TVB 錄影帶是海外華人社群重要一環)某程度上是他們的唯一娛樂,畢竟沒有 Netflix 給他們看 The Crown 配中文字幕。
而現在,卻是一個不只有 Netflix 還有 YouTube 和一切來自世界各地的娛樂的年代。不怕無嘢睇,只怕無時間睇。於是搶飛看《緣路山旮旯》的理由,便不在無選擇,而是一種刻意選擇。
如果你問這批香港影迷,已經離開香港為甚麼還「餓」港戲,他們的回應總少不了這些表述﹕「因為我係香港人」、「因為我想支持香港」、「因為我好掛住香港」。他們買票的原因,其實與寫信師寫信是一樣的,那還是保留香港人身分,維繫與香港的連結。
海外的香港人,縱然離開港九新界,仍冀望透過消費香港文化產物,與本土香港人分享同一種經驗、同一個話題。
《如水》編輯部今期特別製作的 infographic《本土與海外港人如何看 MIRROR?》,大概能幫助我們思考這一點。編輯部在《如水》社交媒體發帖,邀請讀者就 MIRROR 隨想五個關鍵字,結果發現報稱身在海外的港人與身在香港的港人,提出的關鍵字有頗大差異。其中可圈可點的是,海外港人會更加聯想到「香港」,而本土港人則明顯較少。是次調查只是《如水》以有限資源進行,嚴謹度與學術研究難以比擬,但仍能讓我們猜想,會否正是海外港人想要連結香港的冀望,令他們無論看甚麼聽甚麼,也會用一種「香港呀香港呀」的眼光,因而變得與本土香港人的觀點角度不同?
愈抱持「想與香港同步」的心態看事物,就愈無法與香港同步,因為本土香港人看事物,是不會想與香港同步的,他們已經在香港了。
這是否意味一種近乎宿命性的悲哀?好似主理今期《如水》大舞台的藝術家梁洛熙言,就算每天回溯一些「原相片」,記憶、時間和感受也好像無法避免隨著日子變得模糊,「人們自主奮力守護記憶,卻無暇察覺不由自主地流失在定格之外的種種」。這話簡直可以做為奇奇文章《譚仔米線——遊子的語言與鄉愁》的總結。這位居台作者想念譚仔,打開 YouTube 學煮譚仔,「逛了附近兩家連鎖超市都找不到淡奶」,結果換成牛奶卻「又擔心奶味太濃會毀掉整鍋湯底,因此僅加了一湯匙左右」,花約一個半小時最終只換來「米線色澤與我記憶中譚仔酸辣米線相差甚遠」,味道雖也不是全然不像但終究只「有七八成相似」。
「邀台灣室友一同品嚐。她說,酸辣重口,好吃。我笑言:『你吃的是我的鄉愁。』她愣了愣,大概不懂我在說什麼,便自顧自地一口接一口吃完整碗米線。」
注意到海外與本土港人可能無可避免愈走愈遠的,還有今期投稿的讀者雨果。不過較之於哀愁,他的觀點要積極得多﹕
「至於身在海外的香港人,基於沒有來自政權的壓力,可以完整地保留他們記憶當中的香港文化,但是時間過得越久,本土與海外的時間差就越會顯露。故此,海外或許會成為香港文化的時間囊,可以留住某個時刻的香港文化。然而,海外港人同時面對所處地域文化與香港文化的對照,對比之下更能認清香港文化的本質與特徵。是故『本土的妥協與隱語』、『海外的保存與對照』可以並行發展,同時盡可能體諒與認知彼此的狀態。讓我們成為彼此的他者,筆者相信將會是對抗『中國立場的維穩詮釋』的良方。」
這種想法有趣之處在於,當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留=靜」、「走=動」,雨果卻反過來提出「走」的人是某個時間點的香港文化保存者,而「留」的人反而對應著不斷變動的香港文化。這種觀點睿智地抓住了海外港人仍然堅守某個(二零一九年定義的)香港的執著,卻同時也令反映了海外港人面對香港文化時可能出現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執著可能帶來的停濟不前。
文化者,紋理的變化。不變化就是「食古不化」。我不是無限擁抱多元差異、否定捍衛固有原則的原教旨左翼人士(即左膠),但也認同沿地踏步的文化無法成長。而講到變化,「海外」這兩個字特別重要,對香港而言尤是。在茵蔯的《香港音樂與電影小史﹕從誕生、蓬勃到今天》,我們就可以從香港曾經紅遍國際的音樂和電影看到文化上的「外國勢力」如何「干預」香港。
「. . . 顧家煇 . . . 獲邵逸夫及方逸華資助到美國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留學,有機會系統地學習傳統樂理知識,亦是該校首位華人學生。. . . 顧家煇的曲活用粵曲小調,配以簽名式細密連綿的管弦樂,成功為各種探討香港新舊文化衝擊的故事,或重塑華南傳統價值的劇集,注入現代化的演繹。」
「可是在踏進八九十年代紅遍亞洲的豐盛期以先,粵語流行曲在七十年代遇上更大震撼——來自東瀛的流行文化。. . . 香港的電視台就引入「人衫俱靚」、製作精美的日劇,比如大受歡迎的勵志片《青春火花》(以排球為主題)、《綠水英雌》(以游泳競技為主題),還有連杜琪峯都深受影響的《柔道龍虎榜》(竹脇無我主演)。. . . 」
「八九十年代粵語流行樂壇另一現象,就是對來自鄰近地區的歌手兼收並蓄。葉蒨文本來一九七九年於台灣出道,一九八三年開始在港發展,雖然廣東話不算流利,但仍以細膩的歌聲贏得一席之地。同樣來自台灣的有唱作人羅大佑,他一九八六年離台到香港闖蕩時已經成名,為商業掛帥的樂壇帶來關注政治的聲音,當中以他包辦曲詞的國語版〈東方之珠〉(1991)和林夕填詞的〈皇后大道東〉(1991)為代表作。」
如果我們今日鍾愛的香港文化,本來就源於吸納各家所長,而今那麼多香港人身在海外,想像香港文化時卻反過來只往內望,甚至如雨果所言,以保存、守護(保守)的態度看待,這會不會有點浪費?
流散社群能為香港文化所做的,難道真的只有原地踏步?
已經有愈來愈多流散香港文化工作者思考這個問題。我請大家一讀 Weiwei@DDDDDHK 今期文章《Rebrand 香港民主女神﹕如何讓女神「走下去」?》。Weiwei 是一名居於日本的專業香港設計師,文章主要記錄他如何為香港人抗爭重要 icon 之一的「香港民主女神像」進行 rebrand 工作。
本來站起來「撐住」的民主女神像,開始「向前行」。
「. . . 從站立到行走,也蘊含起義到行進的象徵意義,亦以行動性去幫民女解放雕像的靜態,同時流動的形象也呼應著流散港人的狀態。. . . 走下去——這就是我們對民女 rebranding 的答案,也是我們希望向後抗爭時代港人傳達的訊息。」
至於「向前行」具體而言即是做甚麼,答案可以有許多。首先,我認為有一點應可說是香港人(無論本土或海外)共識,那就是拒絕止於「賣慘」。誠如 Weiwei 所言﹕「面向國際,我們也不要再賣慘了。要從爭取同情與支持,變成認同和真心的喜歡」。本期受邀書寫的兩位文學人大概也有類似想法。
沐羽的《寫好香港故事》提到這點﹕
「. . . 在二零一九年以後,香港作家在台灣投文學獎的作品內容開始大幅轉向了書寫抗爭。當然,抗爭是寫作時無法繞開的事件(Event),它有創傷的意涵,導致在此以前及以後發生的事情,我們都傾向與抗爭綑綁在一起思考,好似過往一切事情都終結於抗爭,而日後所有事情都自它出發。而這也直接導致了一件事情:抗爭文學太多,但質素卻不一定高,更有種拿我城創傷去投他國文學獎來換取價值的意味在。」
而鄧小樺在《已經是秋天了,讓我們再遊牧》,亦提到「I don’t want to be a victim, I want to be a fighter」。So how to be a fighter?鄧就談及將會在台灣主理新出版社「二〇四六」,「開創期是希望以香港不能出版、在台灣以至海外的香港人之虛構創作為主打」。她直言,文藝創作不易賣,但二零一九年後的香港作品,也確實有它的市場——不是因為賣慘,而是一些作家,確實漸漸能夠把二零一九年以來香港發生的事,漸漸轉化為更加寬廣、對不熟悉香港的讀者都有意義的作品。例如(前文提及的)沐羽和另一作家梁莉姿﹕
「它們(兩人的作品)都是以相當文藝的方式寫就,但它們本身的小說語言都帶一點港式風格,不止是在文中使用粵語這麼簡單,而是整體語言風格的輕捷直接(同時又有作者自家風格),與台灣本來的文藝小說語言有相當差別,可以讓非純文學圈的讀者進入。有不止一位台灣出版業的前輩高層向我表示,這些小說和台灣現在的小說都不一樣,它們可能會為台灣的小說書寫帶來良性的衝擊。」
也有一些文化工作者「向前行」的方式,是考慮如何把香港帶給更多外國觀眾。如日巷在《「點解仲要講香港?」 在英香港文化人的掙扎與困境》記載三名在英文化工作者如何稍微 twist 一下講述香港故事﹕
「所以 Carrie 指,要讓英國觀眾重新留意香港,『需要一個契機』。她便說起自己的作品 before s/he disappears。在這件作品,Carrie 於展覽場地擺設兩個螢幕,分別投影出香港及倫敦的影像,一對已分手的男女分別講述自己的心境,觀眾在聆聽後可以投票選擇想繼續聽誰的故事。『這件作品背後所強調的是二人為甚麼會分手,其實就係因為二零一九年。我希望話畀觀眾知依家是香港一個世紀最大的移民潮。好多屋企人因此而分隔兩地,導致不少關係破裂。』Carrie 希望以情感作為出發點,讓本地的觀眾能理解到港人正在經歷的事。」
「『我們試過用好多唔同方法去同(英國)本地人講香港的故事,最初係好直接咁講,但原來對方係提唔起興趣。所以我開始轉方法,就係用返佢哋的故事令佢哋明白。』他曾經與一位威爾斯的朋友解釋香港的事,但朋友卻不太理解並以 Hong Kong Chinese 稱呼他,Calvin 見狀便開玩笑說:『咁我可唔可以話 Welsh 係 English?』以此作為例子,『佢就明白當中差別』。」
另一篇文章,則提到香港巴膠移民英國後,如何繼續他們的興趣,「經歷香港所沒有的巴士體驗」。
「『在英國,官方及民間對保育巴士都比較開放。例如會容許舊巴士在周末重新在原有路線行駛,讓市民上車感受,這才是最好的活化。』」
如果「巴膠」的故事不夠傳奇,也許你還可以看看阿域自述《由屋村仔到英軍樂手》,談他來到英國後,如何加入英軍成為樂手,又如何反思香港。
「在軍樂隊中不乏頂尖樂手。別說是工作上的合作,就算是和他們平時閒談,說起嚴肅的音樂話題,也使我大有裨益。我也終於明白自己的瓶頸在哪。如果困在一個城市,就算練得多好,終究是閉門造車。大家都愛到外國進修,不單單是為了一紙証書,更多是啟發和靈感。」
「香港最後一年時,年輕人承受的欺壓都揪著我的心,使我深深體會到一介文人在亂世之中是何等無能為力。那時我就很想令自己變強,去保護弱小。」
「變強的結果是美好的,過程卻是無比痛苦。通過殘酷的訓練,我終於理解到,自己的弱小不在於身體,而是意志力。」
「也是為何當我在通過軍訓正式回歸樂手後,多了一份榮耀感。這是我在當軍樂手和平民樂手時的最大分別。」
「以前,我的音樂只是在表達自己,而現在,我是代表著軍團、國家,必須腰板挺直、無比自豪地演奏。」
此外還有四手聯彈,由四位插畫家瑪珂、日巷、Justin Wong 和 vawongsir,自行擬定一個主題來畫。他們選了香港的街道。不在香港的人卻偏偏選香港來畫?果然,結果沒有令人失望,因為四人畫的都不僅僅是原樣的香港街道,更是他們站在海外,有意無意消化自己身在外經驗後所看到的香港。
誰知道五十年後、一百年後,史家回望二零二零年代的香港文化發展,這些海外港人帶來的新觀點會否成為一個註腳?
最後聊聊「向前行」的心理條件。
其一是信心。香港人要對自己的出品有信心。今期《如水》有來自香港的第一手報道,由艾雲記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現場,特別是有關於 MIRROR 的內容。這個研討會今年已是第十屆,於恒生大學舉行。根據艾雲記錄,談論 MIRROR 時大部分內容都與香港本土脈絡相關。與會者詳細分析了幾個關鍵問題,如「點解 MIRROR 咁紅」、追星其實是追甚麼、「鏡粉」與創傷後香港的關係等。文章深入淺出,就算沒有聽過 MIRROR 作品的人,都會理解 MIRROR 這個香港「社會現象」。與之相輔相成的是讀者莫離的投稿《MIRROR 粉絲的共同體與過渡空間﹕香港文化的社群面向》,同樣將 MIRROR 的成功與二零一九年後的社會狀況扣連,指出「流行文化 . . . 是一個溫室,令我們得以實踐社群生活與公民動員,並從社群生活習得身分認同帶來的責任與力量。」
我們現在已經清楚 MIRROR 與香港的關係。但若撇開香港不談,關於 MIRROR 我們還可以談甚麼?同樣發表於今期《如水》的報道《鏡無限 外國音樂人怎樣評論 MIRROR?》,就反其道而行。記者 FiFi 訪問身在英國的三名非香港音樂人,請他們聽 MIRROR (及其成員)的作品並給予評價。音樂風格喜好當然因人而異,但三位音樂人仍一致認為,「如果 MIRROR 這些『美麗臉孔(Pretty faces)』來英國演出,應該很有市場」。特別是其中一名受訪者 Ziggy,他從姜濤個人作品 〈鏡中鏡〉 MV 那姜濤為自己療傷、拿出碎片的一幕,看出一些意味深長的個人感受﹕「我自己是菲律賓裔英國人第二代,從離散群體的視角出發,逃離一個地方就要割走部分的自己。」
其實香港人早應熟悉這種將文化產品的挪用現象。Kennedy Wong 文章《「香港故事」對抗戰:從〈中國電影中的身分認同、權力及全球化論述〉一書談起》便談述了不少二零一九年及以後,香港人如何「超譯」非政治符號﹕
「然而,筆者認為,身分定義與政治論述的對抗,不一定存在於『政治電影』或擦邊球的藝術作品。一套電影的政治含義,不只存在於電影製作上的構思,更基於觀眾如何『超譯』電影內容,令非政治的對白和劇情,變成『政治化』的共同符號。
在現實生活中,非政治的文化符號經常被挪用作政治反抗。最著名的莫過於二零一七年的『習維尼』。當時一些網民瘋傳迪士尼卡通角色『小熊維尼』,認為它與習近平外表體態相似,該符號遂被中國政府視為違禁圖案。值得思考的是『小熊維尼』的敏感性,是完全脫離迪士尼卡通的內容和本意。因此,就算迪士尼公司下跪道歉,也無法挽回被封禁的現實。這種狀態筆者稱為『超譯』現象,即把一些『非政治』的文化符號賦予新的政治意義,繼而達到綿裡藏針,有如在饅頭中塞入革命字句,廣傳於群體之中。」
「超譯」之所以能夠發生,很多時候並不是刻為之。Alan Alexander Milne 不是為了諷刺習近平才創作小熊維尼,李小龍的 Be Water 也不是他為了爭取香港民主而想出來的口號。莫如引哲學家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的思想,太過著重政治目的的符號,反而限制了人們聯想的空間。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能夠超譯小熊維尼但永遠無法超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再舉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實例。我特別喜歡由亞當執筆書寫,以中國北方廣東歌迷 Saskia 為第一身的個人故事。Saskia 愛上廣東歌,並不是在那個大陸都聽四大天王的年代,也不是在二零一九年之後,而是因為聽 Twins。
Saskia 自言以前也是個小粉紅,令她改變的是張敬軒,或者應該說,是發生在張敬軒身上的一件事。二零一六年,湖南衛視《我是歌手》邀請張參與錄影,但由於他當時被親中人士批評「港獨」,最終所有內容被剪走。
Saskia 說﹕
「幾個月後手機隨機播放到《緋荔榭・少年》,聽到嘅一剎那,我突然意識到,我無可能為咗一啲虛無縹緲嘅宏大敘事,拋棄我從小喜歡嘅嘢。」
「一切都令我覺得好沮喪,但係當我同摯友訴說時,對方建議我唔好執著於張敬軒或者林夕:「除了張敬軒還有別的歌手啊,除了林夕,普通話優秀的詞人也是有的啊,雖然我不知道有誰,但肯定是有的!你不要鑽牛角尖。」嗰陣時嘅孤獨感,比一個人喺 KTV 唱廣東歌更甚。」
「嗰時我開始懷疑一啲我習以為常嘅嘢。」
我覺得這段細節美麗的地方在於,令一個「小粉紅」思考民主自由的契機,並不是因為有誰公開講民主自由的話,或唱民主自由的歌,而是因為作品本身的美麗,令一個歌迷視之為「從小到大喜歡嘅嘢」。又有誰會想得到,張敬軒的音樂會以這樣的方式,改變一個北方歌迷的思維。
所以,我會想問一個問題。對很多香港人而言這可能是政治不正確的,但我還是要問﹕就算我們夢繞魂牽香港的民主與自由,看待文化時我們是否也可以不讓「香港」與「民主」與「自由」成為我們的囚牢,甚至超脫它們,而去發現這些意識型態背後更加寬廣的世界?
我明白我們會害怕貪新是否意味忘舊。我們都是二零一九年一起走過來的,我們不願忘記。恰恰這也是羅依文章《與新青年談舊香港「國族文化」》文末談及的矛盾﹕
為免勞思光《歷史之懲罰》一書提及西方文化「拚命發展力量,而不問『正當』或『不正當』」瘋狂之病、中國文化「只求『態度正當』…… 不能去擴張處理問題所需的實力」癱瘓之症,我懇請海內外香港人發憤圖强同時持守「長遠取向」與「集體主義」兩大價值觀,並戒懼資本主義、精英主義、享樂主義與「權威差距」等習氣揮之不去,腐蝕人心。」
人們常說「行得正、企得正」,後者其實是容易的,前者才是難。行得正又要走得遠,更難了。人如是,抗爭如是,文化亦然。不過,就算走得遠而終於忘本是墮落,怕忘本而裹足不前其實也只是懦弱而已。「向前行」需要勇氣,我相信香港人是有的,大家都相信,這在二零一九年已經證實過。何況香港人這麼喜歡辯論,要是你向前行之後行差踏錯,我相信一定會有人提點(屌)你。畢竟你不只是一個人,而是這個叫做香港的共同體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