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現場
二零一九年後,追星盛載的情感和能量轉化

作為非鏡粉,對追星現場一直避之則吉,本能地抗拒一種狂迷到幾近失去理智的沉溺。今年七月七日 MIRROR 成員 Anson Lo 生日,神徒聚在尖沙咀碼頭慶賀「教主誕」,我才第一次走進追星現場——說是「追」也不準確,因為大家都知道 Anson Lo 不會出現——打風前夕,未行近,老遠已見到一片粉紅海,午後天氣又熱又翳焗,陰沉的雲像隨時要扭出水來,一大班人聚在小小的碼頭空地,摩肩接踵,人聲嘈雜。在這種看似失衡的混亂中,追星的樂趣是甚麼?
十一月五日,我坐在恒生大學何善衡樓,第十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現場,頭炮主題「流行文化」,文化評論人何雪瑩、恒大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和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李薇婷,交出來的兩個與 MIRROR 相關的題目恰巧主題都是關於鏡粉。彼時剛巧過了 MIRROR 成軍四周年,經歷了紅館墮屏事故和漫長的兩個月休團,九展 Viu 總部外依然人頭湧湧,熱潮未有褪色跡象。
學者在研討會上指,MIRROR 真正進入大眾視野,其實是社會運動和疫情之後的兩年間,與公民社會低潮、疫情肆虐等事件密不可分,承載的群眾情感亦複雜多元。研討會回應了我心中的疑問,追星遠不止純粹歡愉,在動蕩紛擾、政治低氣壓的時代,追星其實是「充滿怨恨地愛着」。

點解 MIRROR 咁紅?
「點解 MIRROR 咁紅?」本身也是鏡粉的何雪瑩和鄧鍵一交出的題目,是《分眾環境下的大眾構成:以「鏡粉」為個案》。所謂媒體中的分眾,指的是接收資訊的碎片化,和八九十年代人人都看 TVB 不同,全球化和社交媒體興盛帶來的資訊大爆炸,受眾會自主選擇自己愛看的,即「大家都唔知大家睇緊乜、聽緊乜」。在這樣的前提下,MIRROR 可以紅到「周圍都係」,三歲到八十無人不識,甚至變成「流量密碼」,內容經營者發布任何 MIRROR 相關內容,like 數和 reaction 都有一定保證,正是分眾時代下受眾突然高速聚焦的現象。
為了解構當中成因,何雪瑩和鄧鍵一今年四月底至五月初,招募約六十名鏡粉深入訪談,發現在聽 MIRROR 之前,接近兩成人完全無追任何偶像,一半人完全無聽香港音樂,這些人突然都在這兩年間,不約而同迷上「12 個仔」。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入坑」的時間點,大都在二零一九年之後,「好多人話二零一九年忙緊其他嘢。」
「入坑」點可以完全不同,可能是二零二一年頭的叱咤頒獎禮,姜濤說「香港歌手可以成為亞洲第一」的瞬間,可能是《大叔的愛》、《調教你 MIRROR》,可能是在 chill club 首演 Warrior,「幾唔同都好,只要篤咗第一下,COVID 的時候好得閒,就會上網搵到好多嘢睇,太得閒自然就會睇落去。」
何雪瑩解釋,疫情下突然多了空閒時間,可以被 Viu 和 MIRROR 吸納,背後也反映「傳統流行文化工業威力依然強大」,說的是大眾傳播工具的造星方程式,一來 12 個成員形象各不同,中性的王道的,有乖仔的,也有文青或健碩的,百貨應百客,其次「免費的發牌電視台,有責任填滿 airtime,而因為新,旗下明星不多,既然用相對低的成本捧了一堆明星出來,自然用盡。所以會發現,連續幾套劇都是 Stanley,或來來去去那些人,做晒綜藝、電視劇、電影同歌曲,好似返去以前『歌影視三棲』的年代,聽落好娘,也的確好一段時間無聽過這講法」。
於是無論入坑點是甚麼,在產業既定運作下,都會在短時間內生產大量內容可供「考古」,加上粉絲大大小小群組訊息,各種二次創作如記者會、演出剪輯的 fan cam,為劇集重配字幕、創作同人小說 … 數之不盡,源源不絕,成為豐富的明星文本,結果不論商業廣告還是粉絲應援,MIRROR 都變得隨處可見。何雪瑩透過焦點小組發現,近四成人曾每日花三小時或以上觀看 MIRROR 相關內容,數字驚人,「Gary(鄧鍵一)仲話唔信,我話『你真係唔明』,有 12 個人,每條片睇完官方版再睇埋每個人的 focus,都起碼睇十三次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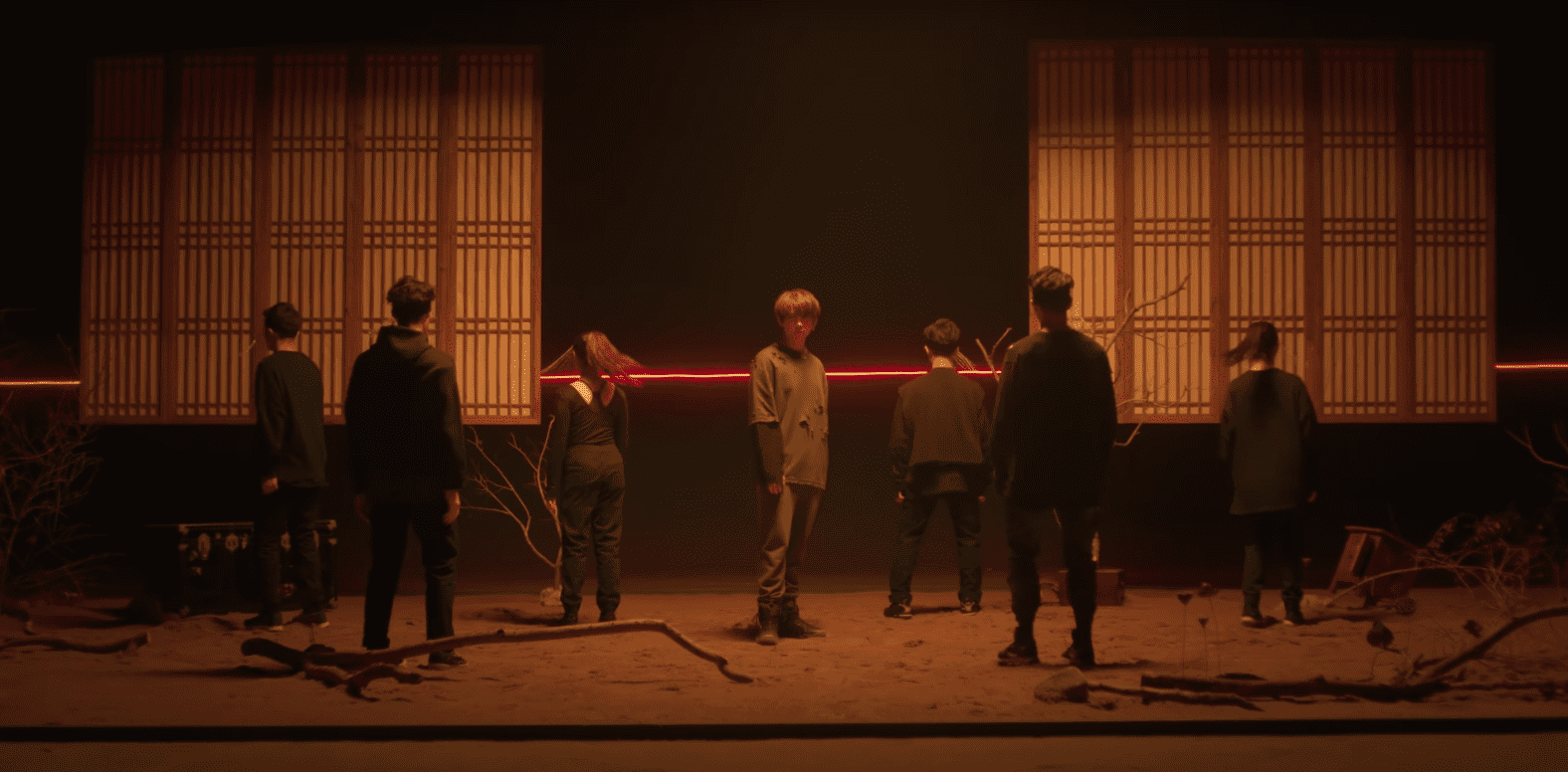
追星追甚麼
何雪瑩也發現,每當鏡粉聚在一起,總會有批評 12 子演藝水平的聲音,例如唱歌走音、舞步不齊等。入了坑,推動這股追星熱潮 keep rolling 的,如果不只是演藝水平,那是甚麼?
回到文首那個「教主誕」的現場,當我開始加入到排隊的行列,無論拍照的、派應援的個個都滿面笑容,「生日快樂」之聲不絕於耳,眼前交談的女士告訴我,和同伴也是剛剛排隊才認識,「邊有人鍾意排隊歎?但排隊識到朋友吖嘛。」排隊行為本身產生社交關係和話題建立的空間,無論結伴還是獨自前來,穿花蝴蝶到處打招呼有之,自在地拍照玩電話有之,轉頭遇人搭訕又結伴排下隊,像細胞的分裂增生,一切在自然流動。
「fans 在一齊,就算偶像不在,自己做嘢都會開心。」何雪瑩的聲音拉回我的思緒,她正分享四月的「姜濤誕」銅鑼灣現場,一班 fans 也是這樣,一班人互講生日快樂已覺得好開心,「大眾繼續聚,好多時候不需偶像在場,純粹是一個 symbol〒〒可能鍾意追星的氣氛,多於個星。」
與其說是追星,不如形容那是大型團契、聚會還比較貼切。回到引言提過的 timing,不能忽視與 MIRROR 熱潮一併發生的,是香港社會在後國安法、後疫情時代經歷的動蕩,公共言論空間迅速減少,公民社會的傳統結社形式不再,「二零一九或二零二零年後,社會好多創傷,疫症下的 isolation,都令傳統結社的方法唔 work。有無新的方法,大家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同其他人連結?」
「人們交換卡、poster … whatever you can think of,同時可以有二、三百檔在免費分享,會讓人感嘆『呢個係咪香港?』大家都好有禮貌好開心,滿足感就是來自這些很淺層的連結,不是很深入的交往,已會令他們覺得好有滿足感。」
這種情感需要,同時剛好在這時被流行文化盛載了。何雪瑩認為是因為文化產品有其開放性,讓人可任意詮釋,以廣東歌復興熱潮為例,「近幾年好多人話,以前上一輩啲歌無 feel,新嘅廣東歌有共鳴,共鳴其實是甚麼?」她在焦點小組邀請參加者挑選近年引起共鳴的歌曲,有一半人提到去年 MIRROR 的 Warrior,成員 Edan 的〈一表人才〉,有人覺得是情歌,但也有人覺得「我過得並不好/但是我會活著」是影射崩壞的社會現況。
同一句歌詞,每個人的理解都可以存在差異,即是所謂開放性。就算是勵志歌,近年的勵志也更偏向「光明與黑暗」並存式的勵志,承認人會失敗,但大家無論如何仍可一齊同行,「如不安伴你經過便能硬朗」(MIRROR One and All),「詮釋永遠是開放的」。
既開放,同時也曖昧。例如有人會認為 Warrior 或 Master Class 是講世代矛盾,令人聯想到對固有勢力的不滿,例如現時兩個免費電視台,一個代表建制,一個不是,「但當你深入同佢傾,佢又知唔係;佢哋覺得,keep 住唱廣東歌,就係忠於香港,但傾入去,中間又有好多 negotiation,係咪真係咁簡單,又唔係。」
「我們理解,追星其實是二零一九年之後,社會重建 resilience 的其中一個 project,和散步又好、燒賣關注組這些都一樣有相類似的地方。雖然那種連結的公共性,未必是同以前一模一樣。」

鏡粉作為社群
無獨有偶,中大文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李薇婷的研究《韌性與任性:「鏡粉」與創傷後的香港》,進一步探討了「鏡粉」群體的韌性,在公眾輿論規範下的回應。她發現,在公眾輿論中,鏡粉通常被強調的特質,是「好多人」,和被認為是非理性的消費行為,如課金、集資應援;被肯定的,則通常與社會參與有關,如公益等。
其中一個常被強調的名詞,是「理性追星」,無論在公開報道、評論中,或是連登討論區的相關貼文中都會看見,諸如「粉絲行為,偶像買單」一類的口號,用以劃分理性和非理性的行為,但其實並沒有客觀準則。
她亦提到,不同事件,例如何桂藍在 47 人案庭上哼姜濤〈蒙着嘴說愛你〉的「So I say I love you」,都令外界在社會崩壞、致治高壓時期中,將「鏡粉」和公眾議題、政治事件聯想在一起。


仲講 MIRROR,悶唔悶?
這是前往研討會之前心中的疑問,MIRROR 自 ViuTV 的《全民造星》出道都已是二零一八年的事,感覺像是上個世紀。不過轉念一想,他們紅起來原來又只不過是這一兩年的事,如主持該討論環節的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言,了解 MIRROR 熱潮,也是理解社會這幾年發生甚麼事的一塊鏡。
「是二零一九年後,經歷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去思考創傷和重建的關係 . . . 兩份論文着重在群體的一致性,同時當中的情感非常 diversify,我看到好多恨和好多愛,這種狀態好表達到一個社群應該有的 diversity。」
鏡粉的圈子有不同大大小小群組,每個成員有官方 TG group,從中分裂的群組更是不計其數,是非爭議少不免。但對外時鏡粉大多對鏡粉社群有不同程度的維護,例如有時他們會強調,自身言論不代表其他鏡粉,何雪瑩也說,鏡粉飯圈「日日都嗌交,但有時對住成個 MIRROR 的 hater,會槍口一致對外。組織內部會不斷分裂,志同道合的人會走在一起,基本上人類組織會出現的問題,在鏡粉圈都會出現」。

研討會近百人出席 創辦人呂大樂﹕香港研究仍有 大把題材可做。
香港社會與文化研討會始於二零零一年,由一眾熱衷香港研究的學者每兩年舉辦一次,專為香港研究提供跨院校、跨學科及跨世代的學術交流,讓粵語發表、中文書寫的學者有專屬的發表論壇。上屆研討會因疫情關係以線上形式舉行,所以已是事隔四年再辦實體,吸引近百人到場。今屆研討會除了「流行文化」,另設有「鄉郊島嶼」、「知識思想」、「脆弱社會」和「數碼技術」主題。
每個主題講者發言後,設有討論和觀眾問答環節。討論最熱烈的是「知識思想」環節,共發表了三份研究,題目包括「學生作為解殖者:1960-1970 年代的《學聯報》」、「新左翼國際主義、離散中華民族主義及吳仲賢的安那其願景」及「金庸的國族思想:《明報》中的「文革」話語」,有觀眾質疑明報社論並非全出自金庸手筆,也有人問在今時今日的香港討論安那其主義的啓示,及吳仲賢在政治主張上的轉變等。
其他社會向的研究包括,周思中追溯殖民管治下的沙頭角地理,本身是南丫島民的梁寶山,在「明日大嶼」背景下做島嶼研究,反思發展為島民生活帶來的衝擊和挑戰,梅窩居民兼土地教育基金總幹事龍子維介紹大嶼山農業史。中大學者陳盈研究疫情下劏房戶的糧食短缺與精神健康的關係;鄧鍵一和浸大學者袁瑋熙研究社會穩定性對青年選擇工作、生活模式的影響,嶺大學者譚以諾,則研究在近年本土創意產業似乎出現復興時,創意勞工的社會脆弱性有無改變。另外,亦有學者研究疫情下的 factchecker 如何構建事實,及香港互聯網使用者的數據素養。
研討會總結時,有份在二十年前開始舉辦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的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教授呂大樂憶述,當年與友儕聚在一起,在他家天台飲住酒,對了一句「極其苦悶,不知如何是好」,興起辦粵語發表為主研討會的念頭。歷年有不少有趣題目,如麥嘜、陳慧琳,亦有不少議題與社會事件相關,如七一遊行、蘋果日報現象、社會運動等,那是政治傳播學作為顯學的年代,時移世易,今日看似是最壞的年代,學術研究還可以如何走?
「做研究或做知識探索,常會遇到好似唔知點行的處境,二十年前也是這樣,只是原因有點不同,現在政治、文化環境變了,但是否代表無得行、無題材?今日見到,仍有大把題材可做。宏觀大環境的變化,就算有時撩住撩住痛,亦可能刺激我們重新審視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香港的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是庶民、平民的角度,日常生活普通人感受的東西,都想重視和研究,背後總有些道理,這觀點仍是香港研究很寶貴的地方。」
「做文化、社會研究,最終想做甚麼?是想有 impact,是你去同個街坊講,佢會覺得都有過癮的地方,有得着。」
(本文經過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