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完美之茶杯、或曰 2022 年的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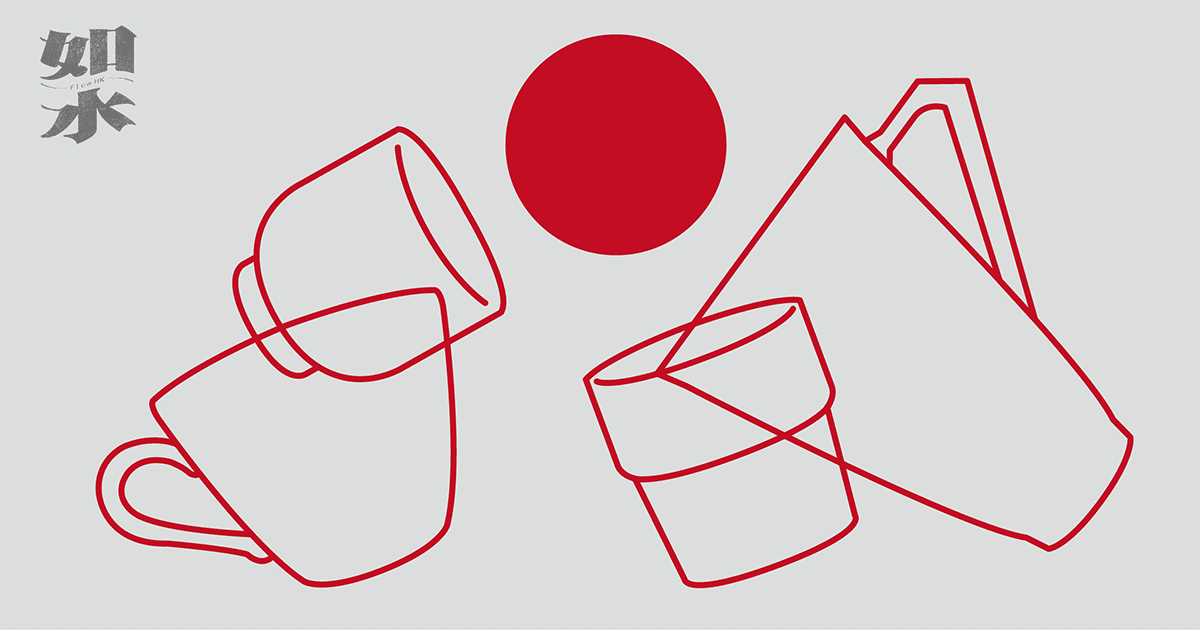
一切都從尋找一只完美的茶杯開始。
搬家的決定來得很倉卒。塵埃落定,以為我終於可以好好坐下來喝杯茶了,才發現自己需要新的茶具。之前居無定所,都是隨便湊合着,現在找到落腳點了,便覺得是時候投資屬於自己的茶具。
受過多種茶文化薰陶的我很好奇德國在這方面有甚麼可取。雖然近年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茶熱,但傳統的德國茶具幾乎不存在:基本上茶具與咖啡具二者並無區分,而且看起來非常笨拙,是更精緻的英法設計的拙劣模仿。另一方面,在柏林時髦小區的精品店可找到色彩繽紛的葡萄牙製當代北歐設計陶器,賣茶的專門店也有售傳統的日本茶碗。然而北歐人設計那些無耳杯的對象大概是 Cappuccino 而不是茶,傳統日本茶碗或功夫茶具也不完全適合廿一世紀的日常生活,儘管現在很多的文化復興運動,東亞人正透過精心重演古典茶道儀式與散發「正宗」東亞美學的佈景和服飾重新發現他們的傳統,並使之成為一種非常 Instagrammable 的小眾時尚。
亞洲人自我異色化可怕,還是西方人挪用東方文化更為糟糕?一次逛宜家,在餐具區發現一些「和風」系列,但那些半桶水的模仿讓人感覺很不爽。它們是為從未用過茶杯或飯碗但又喜歡這種「東方時尚」的人而製的。對亞洲人來說,那些形狀、大小、比例、顏色圖案、觸感全都不大對。穿過其他區域前往出口時,有些甚麼吸引了我的注意。園藝區一個架子上,放著餐具區沒有的藍綠色小陶杯──原來它被歸類為迷你花盆。 但對我來說,它比起剛才餐具區中被稱之為茶杯的所有其他東西都更像是茶杯。
開始研究茶杯的歷史時,我發現人們剛開始喝茶時,專門為茶而設計的飲用器皿尚未存在,因此人們就隨便使用手頭上的東西。在日本,始於十五世紀並以千利休為代表的「侘茶」運動,挪用了從中國和韓國進口的日常使用的廉價陶瓷碗,最終演變為我們所認知的日本抹茶碗。所以,就像千利休在一只飯碗裡看見了一只茶碗一樣,我也於一只花盆找到一只茶杯。
日本茶碗的故事並未結束。2014 年至 2015 年旅居日本期間,我曾經歷了一場語言危機:搜尋「飯碗」時,發現它並不存在;搜尋「茶碗」時,飯碗卻出現了;明明也叫茶碗,我卻花了很多時間,才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茶道茶碗」類別下找到抹茶碗;迴轉壽司店那種日常粗用的直筒茶杯則叫作「湯飲」(熱水飲用器皿之意)。這就是日式演繹有欠準確的地方。
能指與所指之間不穩定關係的例子還有的是:一天我們上了 Mulackstraße 一家時髦(且「正宗」)的日本茶室,並點了抹茶。櫃檯的日本女生以德語提醒我(來了柏林三年,我仍未習慣這裡的亞洲人以德語而不是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般以英語或其他東亞語言跟我說話:即是說,我不習慣他們沒有根據我的外表而對我的出身作任何假設),他們的抹茶是盛在 schale(碗)裡的,而且不加牛奶。她可能只是出於好心,想確保我知道自己點的是甚麼,但我卻有點奇怪她竟覺得有需要向我澄清這對我而言是理所當然的細節。也許所謂理所當然的東西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就像人們都理所當然地覺得茶是一種放在茶碗或茶杯裡喝的熱飲,直至 1981 年伊藤園出產了世界上第一瓶瓶裝烏龍茶。就像印度奶茶和抹茶越洋過海後經歷異變/基因突變,變成了「chai latte」和「matcha latte」,並被重新定義。因此,我們究竟是用碗、(有或沒有把手的)杯還是塑膠瓶(甚或花盆)來喝茶可能並不那麼重要。形式為功能存在,而兩者都是流動的。
現在是閱讀岡倉覺三(Okakura Kakuzo)的 The Book of Tea 的最好時機。隨着茶在西方世界再度流行,這一部經典著作重新被搬上神枱。除了書中對中國和日本的茶歷史與哲學的深入研究,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本小書原文就以英文撰寫,並於 1906 年在美國首次出版。它並非當時西方 Japonisme 熱潮中被翻譯及挪用的產物,而是由岡倉本人帶着向西方介紹茶道,以抗衡主流西方文化的明確目的而撰寫,而當時明治維新的知識分子普遍都批判日本傳統文化而主張擁抱西方模式。多得岡倉的影響,京都和奈良才逃過了於二戰被美軍炸毁的命運,今天我們才得以享受古都風情和抹茶甜品。但重點是,一個世紀前的西方竟有另一個亞洲僑民試圖向極其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世界解說茶與東方世界,實在很讓人有種奇異的滿足感。
怎麼我們好像從未聽過類似的關於中國茶和茶具的故事?眾所周知,最好的白瓷來自景德鎮,但我未見過有人像收藏 Wedgewood 或 Spode 那般追求優質的景德鎮茶具。Edmund de Waal 在 The White Road 中講述了他的白瓷起源朝聖之旅。我對茶杯的調查主要在網上進行,De Waal 以第一身探索白瓷歷史的嘗試跨越了時空,從中國景德鎮,到法國 Versailles 與 Limoges ,德國 Dresden 與 Meissen,再回到起點的英國。我嘆服 De Waal 對中國瓷器歷史知識的淵博,同時發現不期然間我竟也走過一條類似的軌跡:從香港到英國、日本、法國,再來到現在的德國。不知不覺的,我也走上了那條白色之路,心中念着棕與綠,以及其容器。
還以為在柏林要找 Dresden 瓷器很容易,但我更常遇到的反而是東德製造的 Jäger Eisenberg 仿青花瓷。它有其有趣之處,具有一款獨特的稻草圖案與 Art Deco 形狀,在我位於前東柏林的新居是不俗的裝飾,但並不是我會經常使用的東西。2021 年夏天搬家之際,隨著疫症限制略為放寬,我們去了一趟 Dresden 短途旅行。由於沒有時間專程前往 Meissen,我們只參觀了專門店,結果也沒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我開始明白為甚麼 Edmund de Waal 說 Meissen 是一場試圖模仿中國的法國的實驗失敗結果。
奇就奇在我竟也去過 Limoges 好幾次,但每次也不過在火車站稍作停留。因此對於這白瓷之城我所認知的只有那座宏偉的石與鋼鐵組成的十九世紀建築,和其前方相當荒涼的後工業公車站。如同 Dresden,閃閃發亮的白瓷被隱藏於沾滿沙塵的灰色石頭和混凝土背後。Limoges 是我們送迎一名擁有一半英國血統和一半法國血統的城堡女主人的親友的地點,她的 16 世紀城堡位於 George Sand 所在的 Berry 地區的鄉郊,距離 Limoges 約一小時車程。數年前我第一次造訪,本是想去學習一些「正宗」的法語和文化,沒想到在這個以英國人為主的家中,我幾乎是會講最多法語的人。這裡不見 Limoges 瓷器,卻有大量的英國骨瓷,仿明青花瓷杯碟茶壺等排滿了整幅牆壁。有些人對於我稱呼那些繪有藏於寶塔與垂柳之間的幻想東方景緻的奇觀 Chinoiserie 為「那些冒牌中國貨」感到很好笑。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些擁有這麼多華麗的 Staffordshire 茶具的愛茶的英國人,喝茶時都只是在馬克杯中放一個茶包。
我唯一遇到 Limoges 白瓷是在當地的市集,零丁或成套的茶具食具都以不能置信的超低價出售。對門外漢如我來說,所有白瓷看起來其實都差不多。無論是 Meissen、Staffordshire 還是 Limoges,都是被花卉或其他裝飾圖案所淹沒的白色粘土,形塑成浪漫的 Rococo 風格,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極其脆弱而且完全無法保溫,總之就是裝飾性多於實用性。與茶一直是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東方不同,茶在西方是一種奢侈品,西方茶具設計不為實用,而是為裝飾性的華麗。
回到柏林,又有一次奇妙的偶遇。我花了幾歐羅,從一位德國老太太那裡買到了一件非比尋常的東西。雖然我見過很多西方製造的 Chinoiserie 瓷器,但我這還是第一次遇到景德鎮出產的仿明青花 Chinoiserie 花樣的英式茶杯連茶托。我知道中國有製作專門為出口西方市場的產品,但見到東方人親身參與這場西方異色化東方的計劃,仍是令人震驚的。難怪那些英國人會以為他們的 Chinoiserie 是「正宗的」中國產品:誰又能說得清呢?
「咩係正宗? 好味咪正宗囉。」香港著名美食評論家蔡瀾在電視螢幕上展開他趣怪而寬容的招牌笑容。我們對所謂正宗是如此執著,以至那評語聽上來簡直有若褻瀆。那是頓悟的一刻。Edmund de Waal 在書中說他早就放棄了「正宗」。早於我的探究開始時,我便知道這兩個字本身存在問題。追溯得愈遠,距離正宗也就愈遠。結果正宗就是對你來說感覺對的東西。手感恰到好處的茶杯,熱茶的香氣,喚起往昔快樂的日子。
Heimweh(家的痛)在德語中是鄉愁的意思。從我於海外生活的有限經驗中,我知道 Heimweh 是發生於味蕾中的。每次搬到一個新地方,總會有人問,你最想念家鄉哪種食物?我的答案一定是茶,尤其是港式奶茶。對我來說,港式奶茶是正宗的,不僅因為它比「原裝正版」的英式奶茶好飲得多,也因為它對我來說別具意義。港式奶茶專用的厚身碗形白瓷茶杯與茶托毫不優雅但日常可親,為流散生活中的所有混亂失序提供了一個舒適安穩的空間。2019 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隨後泰國、緬甸、印尼亦相繼發生政治抗爭……人們開始談及象徵團結的「奶茶聯盟」。茶是我們的語言。一個異鄉人在一個不懂得我的茶的語言的異地,我重新審視遠在北美洲、已然蛻變成美國人的親戚,想到華裔僑民的離散史,並第一次感到心裡抽痛。
我覺得自己有必要保存這神聖的遺產 ── 一種味道、一種觸感與空間感、一種將我與我失落的城市聯繫起來的儀式。環境轉變,於是我們向前看,但該留下多少,又帶走幾多?該像明治維新的知識分子一樣擁抱新事物而拋棄舊事,還是像岡倉或現在那些茶文化復興主義者那樣義無反顧地堅持自己的根,甚至在面臨身分危機的時刻嘗試將之重新創造?我們能接受多少轉變,而又不離其宗?在這全球化、大規模流離失所、種族意識和解殖的時代,多元文化主義、文化同化、文化挪用和民族主義運動意味了甚麼?也許,在尋找一只完美的茶杯的時候,我其實是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
撰於 2022 年 7 月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