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籠裡的娛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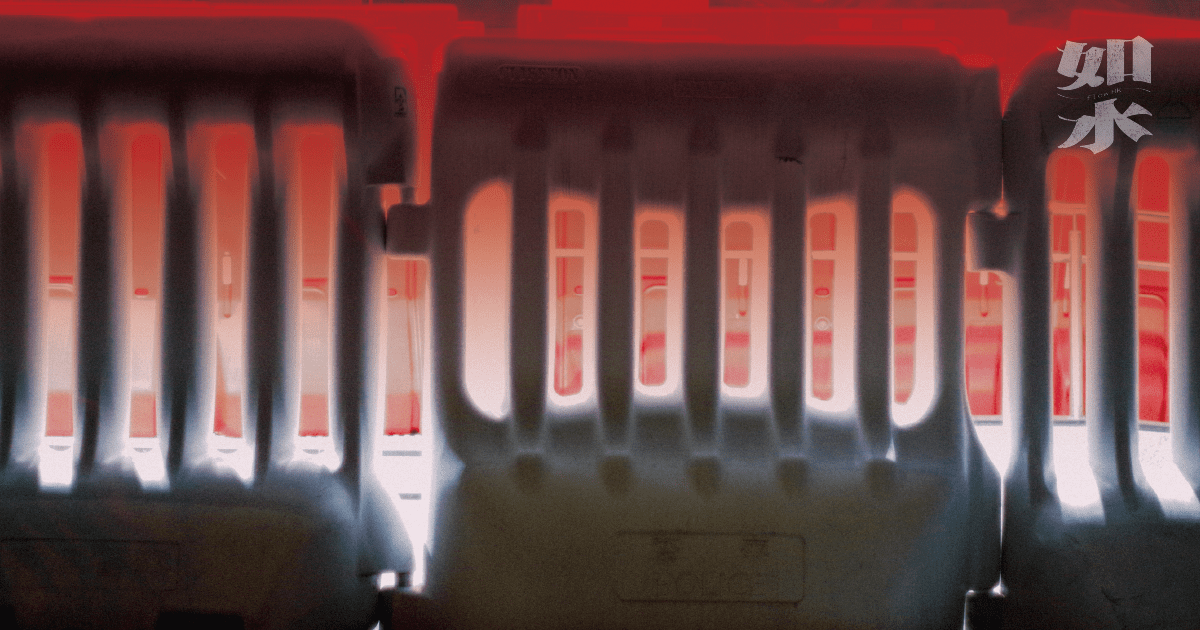
疫情與國安法雙重打壓下,香港在過去兩年陷入無盡深淵。一方面防疫政策不斷蠶食個體自由,壓抑意志;另一方面港共屢屢祭出國安法使公民社會分崩離析,許多熟悉的人、事、物或解散或被直接囚禁。時勢真惡,每個人身邊不是有著離港移民的親友,便是正打算離開。去留不僅是一個長期熱門討論題目,更成為一種詮釋「香港」差異的現象。
離開的人與留下來的人之間的差異,可以從近期何桂藍的一篇文章窺探一二。何桂藍在 Patreon 上一篇文章〈 內疚是不是會令人感覺變鈍?〉與藝術家白雙全商榷,因為白雙全選採了他與何桂藍的通信創作,刊登在明報。然而何桂藍認為白雙全懷抱過重的愧疚,詮釋獄中的她「 故作輕鬆」,並說無法以日常的語言回覆她。即是白雙全創作一刻,他已認定獄中的人只能終日恐懼,僅能透過信紙被刪去的錯別字或字句釋放內心真實情感。
我們即使身在牆外,或身在香港外,但是何處不是囚籠?囚籠內外的張力一直存在,並愈演愈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歷史押了韻,過去一年香港本土娛樂發展卻迎來爆發,電視劇、綜藝節目以 Viu TV 為首,Mike 導推出的〈 ERROR自肥企劃〉被認為以綜藝探討娛樂與人心的關係。廣東歌壇亦百花齊放,組合「MIRROR 」引爆追星熱潮,把銅鑼灣變成「姜濤灣」。然而另一方面,香港亦終於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禁片,一批反映反送中運動的電影無法在香港上映,只能海外飄流,周冠威《 時代革命》奪得去年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任俠、林森合導的《 少年》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定居澳洲多年的羅卓瑤以雨傘運動為題的《 花果飄零》奪金馬獎最佳導演。而留下來的人可以看《 梅艷芳》,票房斬獲甚豐,但不少評論直指電影選擇性呈現梅姐生平,隱去她當年參與黃雀行動營救六四民運人士,以及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的史實。新導演想拍片言志,不過電檢擁無上權力,動輒要求導演刪剪內容,否則無法公開播映。參加鮮浪潮的短片〈 執屋 〉因為電檢要求刪剪,最終無法播映。縱觀去年青年導演中唯有楊建邦《 十二點前我要返屋企 》取出理大圍城期間眾人的心理狀態,化為人物心象間接拍出年青人承受難以磨滅的創傷,而又幸運地透過鮮浪潮公開放映。
何以興盛與禁忌並存?囚籠內外言志的人即使心同此理,卻總有暗湧起伏,既然心存愧疚,而又沉浸於娛樂享受——分裂的香港,就是當下的現實。我們身處當中就是一片一片的破碎微物,物欲裡縱橫,內心期待與大家重聚。
像巴勒斯坦導演蘇萊曼 (Elia Suleiman) 的《 那裏是天堂 》 (It Must Be Heaven),最後一幕鏡頭定在巴勒坦斯一間的士高內,巴人少男少女在內勁舞。你以為以巴衝突的戰爭狀態都見不到,但是他們即使生於戰亂之地,也會像一般人想玩、娛人娛己。於是在怪異的氣氛下,鏡頭切換到的士高外,受聲浪吸引的軍車停下來,兩名以色列青年軍人隔窗盯著裏面,忽然兩人都不由自主地隨節拍搖晃身體。
娛樂何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承認一點:娛樂無人可以擺脫。娛樂即使使人盲動,但確實能夠打破某些藩籬——當然蘇萊曼刻意留白的是,歌曲播完後,他們會回復正常。
接收與再創造
人類學家 James Scott 說:「 他們能夠認清現實……轉而認為這是一件理所當為的事情;並不是先喊個原則,然後身體力行。他們行動在先,才從行動中找到邏輯。抽象原則是實際行動的孩子,而非父母。」(《 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
一無大台,二無綱領,香港民間在 2021 年不斷把民意民氣轉入娛樂產業,其行動模式大概可以歸納為民意把閱讀娛樂產業推出的文本,吸收並加以再創造,意圖達到與他者聯結的效果。畢竟疫情與國安法雙重打壓下,民間遑論具體動員反抗,連基本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都被打散,每個人的心靈何其孤獨。如「 姜濤灣」,如網上眾多後援會群組,打破疫情限聚令,眾人都有了心安理得在街頭上與人相聚的理由。如是者去年眾多娛樂產業的文本,受此影響下,不少流行文化文本都不約而同取材港人當前面對難關。
以廣東歌在去年的爆發為例,大紅的歌曲當中不少都指向幾種情感——去留掙扎( Rubberband〈 Ciao 〉、MC Soho&Kidney〈 係咁先喇〉、張敬軒〈 On My Way 〉、C AllStar〈 留下來的人 〉 )、離散思考( 岑寧兒〈 風的形狀〉、〈勿念〉)、堅守信望(泳兒〈 荊棘海〉、Dear Jane〈 聖馬力諾之心〉)。九十年代也面對回歸「 大限 」,加上世紀末情緒,當年也有不少探討去留的歌曲,然而當年樂壇仍然以「 四大天王 」或王菲等人的情歌當道,而今日樂壇卻似乎以離散去留題材歌曲為主流。除了有民間閱讀追捧,其實也可以理解成今天的廣東流行曲,離散即是流行,香港流行離散,故此流行樂產業也有同樣傾向,隱晦地帶出當下現象。
詮釋香港的角力
與此同時,2021 年香港娛樂文化也迎來另一種變化——離散與催逼出流行娛樂興盛,但那種興盛很快便面臨來自大灣區的角力。去年香港藝人亮相中國多個綜藝節目,並有意識地自我重新命名為「 大灣仔」、「 大灣妹 」,組軍參與中國綜藝。離散意味打開缺口,打開缺口意味香港詮釋角力步入新的格局,方興未艾的本土娛樂即使比起大灣明星陣來得更由下而上、更有機,但是目前所見,本土娛樂發展的活力與脆弱可說是一體兩面。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雖說廣東歌復興,本土娛樂產業爆發,爭論也隨之而來。像 Viu Tv終究無法擺脫其官方認可的持牌電視台,Mirror 掹車邊拍政府廣告催谷「完善後的立法會選舉」、從 2019 年延燒到現在的「黃藍爭論」、海外港人與在地港人之間的理解差異,抗爭不再,情感轉入其他範疇,能否以某些教條一言以蔽之?我們彼此渴求理解與重建連結,然而創傷與挫敗使感情無所適從,終於再次爭論與無法理解彼此。
如果以對抗大灣仔大灣妹,高舉團結本土文化人的大旗是不切實際。究其原因,我們的心經歷 2019 年後不再柔軟,情感動員來得快去得也快。只是必須點明一件事,詮釋香港的權力隨時有可能被官方定義的娛樂事業所取代,而對不少港人來說,這可能是一條出路,像林曉峰憑大灣仔找到事業第二春,像莫文蔚如此遠離政治的歌手也自號為大灣妹。上至徐克,下至林超賢等香港中生代、上世紀新浪潮導演也在合拍片模式當中找到自存之道,他們可以在愛國動作片《長津湖》、《 紅海行動》等大肆發揮港產片精亮的動作設計,爆破效果,他們一定明白過去港產片言志的生猛活力,早由主旋律取代,但是他們並不介意,只要有資源讓他們在技術上滿足獵奇與野心便夠。
分裂是現實,現實即是多片分裂的鏡,我們是破碎微物,惶惶終日,牢籠不僅限於監獄,無日無之地惡化的社會亦是牢籠。海外港人與留下來的人要明白,分裂無可避免,但是在關於我與他者的關係上,不妨採用立陶宛猶太哲學家 Levinas 的思想。Levinas 是二戰集中營的倖存者,融合猶太哲學,挑戰海德格的存在哲學,提出以他者為中心的思想。簡單來說,我從他者處自有一種責任要背負,他者是我的自我,並非我們累積的知識帶領人走向未來,而是我們以愛與倫理責任包覆的知識可以帶領。要理解 2019 年後的香港,我隱晦地覺得,以「 我 」為出發點理解那個地方,總存在難以解決的謎語,也因此就像去年的一部香港舞台劇名字一樣,《 有你,故我在 》。有你,我才會存在,在世上無數個無止境地艱難的地方生存,看見他者的臉孔,才可理解我們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不僅僅是娛樂,所有發生在香港的流行文化現象,讓你看得到他人之顏,更重要的是讓你知道還有人存在於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