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加坡經驗看林鄭政府的防疫政策
公民社會、安心出行和抗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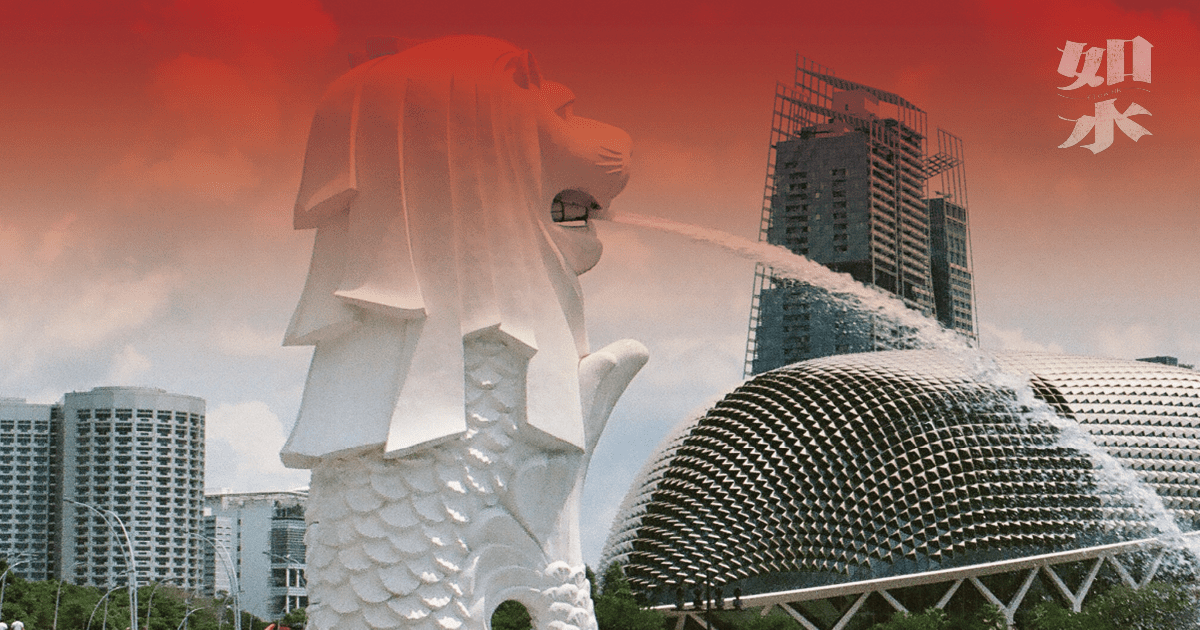
前言
2020 年 3 月中,我飛抵新加坡履新。當時新加坡還未有明確的防疫方向,只是跟隨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後來疫情的嚴重幾何級數上升,於是便於四月上旬開始展開了長達個多月的「 阻斷措施 」( circuit breaker )即封城是也。後來重新開放,之後又分別短暫恢復阻斷措施,推行限聚以及禁堂食等的措施,最後順利過渡到「 堅強抗疫 」,與病毒共存。從新加坡的抗疫經驗中,我們看到一個選舉威權國家如何動員舉國之力,對抗武漢肺炎。
一海之隔的香港在兩年之後開展了其後知後覺的抗疫工作。儘管中國駐香港政府的抗疫政策中乏善可陳,沒有吸取世界各地的抗疫經驗,但是我從新加坡經驗中,看到未來香港政府對箝制香港人的自由的手段。因此,本文旨在以新加坡的案例,指出香港政府所可能採取的一些措施和影響。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之所以在政治科學中不斷被提及,皆因它在民主化、民主鞏固( consolidation )以及社會運動動員等課題中都被賦予一定的角色。在Prof. Larry Diamond 於 1994 年發表的論文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中指出,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與他們強大的公民社會動員能力有關。政治學者 Dr. Dafydd Fell 亦曾經在其專書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aiwan 中指出,台灣的民主化與他們的女性平權運動、環保運動、台灣獨立運動、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之下形成強大的公民社會有關。究其因由,皆因公民社會可以籠統地理解成國家以外的自發、自主、自治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人們可以形成陸恭蕙( 已投共)在 Building Democracy Creating Good Government for Hong Kong 所講的自主關聯網絡(a network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而這個領域和網絡則需要以一定程度的公民自由為前提。
此前一直飽受詬病的現代化理論(Theory of Modernisation)中,曾經提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其中原因包括中產的出現,並繼而導致識字率的提升等。當然,現代化理論與民主化的關係在中國這種透過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tialism)以及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來發展經濟的國家並不適用,皆因經濟發展和中產的出現乃由國家直接或間接主導,並非自主生產決定的產物。可是也曾有學者指出,隨著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從一個草根佔多數的三角形,變成中產佔多數的菱形。這些中產和專業人士在生產活動中逐步作出自主和專業的決定,成為初生的公民社會的雛形,繼而逐步追求在生活的其他面向作出自主的決定。從這個角度看,自由的生產決定,是孕育公民社會的關鍵,而健全的公民社會又會推動民主化的出現與鞏固。那麼,公民社會的形成需以自由為前提的說話,就不言而喻了。
防疫政策所帶來的隱憂:新加坡為例
隨著港版國安法的推行以及香港政府的虐政統治,舊有的「網絡」和「領域 」早已分崩離析,然而新的「 網路」和「 領域 」的形成很有可能在現有的苛法之外再因為防疫措施而進一步遭到限制。
1. 出入行蹤與人際網絡
新加坡為了追蹤武漢肺炎的傳播鏈,在阻斷措施之後推出 Trace Together 應用程式,並要求所有人出入任何處所,甚至是商場內的每一間商店。這個 Trace Together 的應用程式的功能越發推陳出新,甚至有疫苗紀錄以及刊登檢測結果。有一次,在新加坡 JEM 商場爆發武漢肺炎疫情,新加坡當局利用這些出入記錄以及應用程式中的藍牙探測功能,搜查出曾經在患者身邊經過的人,並在應用程式中提醒他們需要進行隔離,可謂佈下天羅地網。
可是,這種做法並非沒有問題和爭議。新加坡當局早前保證這些數據不會用作刑事罪行的調查,但是在 2021 年 1 月時,新加坡國會被「 知會」這些數據同樣會交給警方作刑事罪行的調查,與先前的保證大相徑庭。及後,新加坡國會才通過另外一條法案,限制這些數據只能用於反恐等用途。
放在香港的語境,安心出行可以讓政府掌握更多居民的訊息(而新加坡政府早就大量掌握,詳請可以參考 Sing-Pass ),透過這個科技蒐集這些數據後,經過大數據分析,可以知道一個人的人際網絡、日常生活範圍以及消費等。那麼,任何公民社會自發形成的網絡就很容易被政府發現,以大防疫和犯罪等原因在形成更大的網絡之前撲滅,對公民社會的形成造成打擊。
2. 執法權力過分下放以及互相舉報
在 武 漢 肺炎 疫 情中,新加坡 出現了兩 種 新職 業,分別是 安 全 距 離 大使(Safe Distancing Ambassador)以及安全距離執法員(Safe DistancingEnforcement Officer)。發生爭議的職業則是後者。事源有位新加坡居民Mr. Nick Mikhail 因在其單位被投訴多次舉辦聚會,違反防疫政策,被新加坡市區重建局調查。調查期間,安全距離執法員以及警員同時進入其家居檢查。Mr. Nick Mikhail 指出這些人員在搜查其處所時並無搜查令,因此此次搜查並不合法。然而,新加坡市區重建局事後發表聲明,表示安全距離執法員毋需搜查令即可進入、檢查和搜查違反防疫政策的單位。
同時,新加坡政府的一聯通(One Services)服務手機應用程式在 2020 年也推出了回報功能,讓市民回報違反社交距離的個案。一年之後,當局表示收集到超過十萬宗舉報。儘管新加坡當局並不會跟進每一個個案,但是這樣的風氣一旦形成,就會吸引市民互相監督、互相舉報。
目前,香港政府推出了限制家居聚會的法令,禁止來自兩個家庭以上的人士在私人地方聚會,違者罰款一萬港幣。可是在執法層面上,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都曾經提及不會主動執法。可是,當有政治需要,他們依然可以循新加坡的進路,以防疫為名進行沒有搜查令之下的搜查,而這些搜查的權力或會延伸至其他人員,對公民社會的活動造成嚴重干擾。在全球先進地區學會與病毒共存的時候,限制聚會此一舉動對公民社會在國安法之後的重建、轉往地下化等造成打擊。
同時,在港版國安法推出之後,舉報違反國安法的渠道正式大開,令人心惶惶。因此,如果政府推出舉報違反多於兩個家庭聚會等有違防疫措施的舉動,也會加劇舉報成風的問題。人們或會因為擔心別人舉報,在形成自主的人際網絡之時,失去互信的基礎,進一步窒礙公民社會的發展。
結論
從公民社會的各個層面來看,自由結社以及組織成人際網絡是至為關鍵的一環。可是,從新加坡的抗疫經驗中,這些面向都被犧牲掉。未來在香港「 動態清零」的抗疫方針下,很有可能同樣會出現這種情況,甚至更糟,繼而影響香港的公民社會的轉往地下或者重新興起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