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書評】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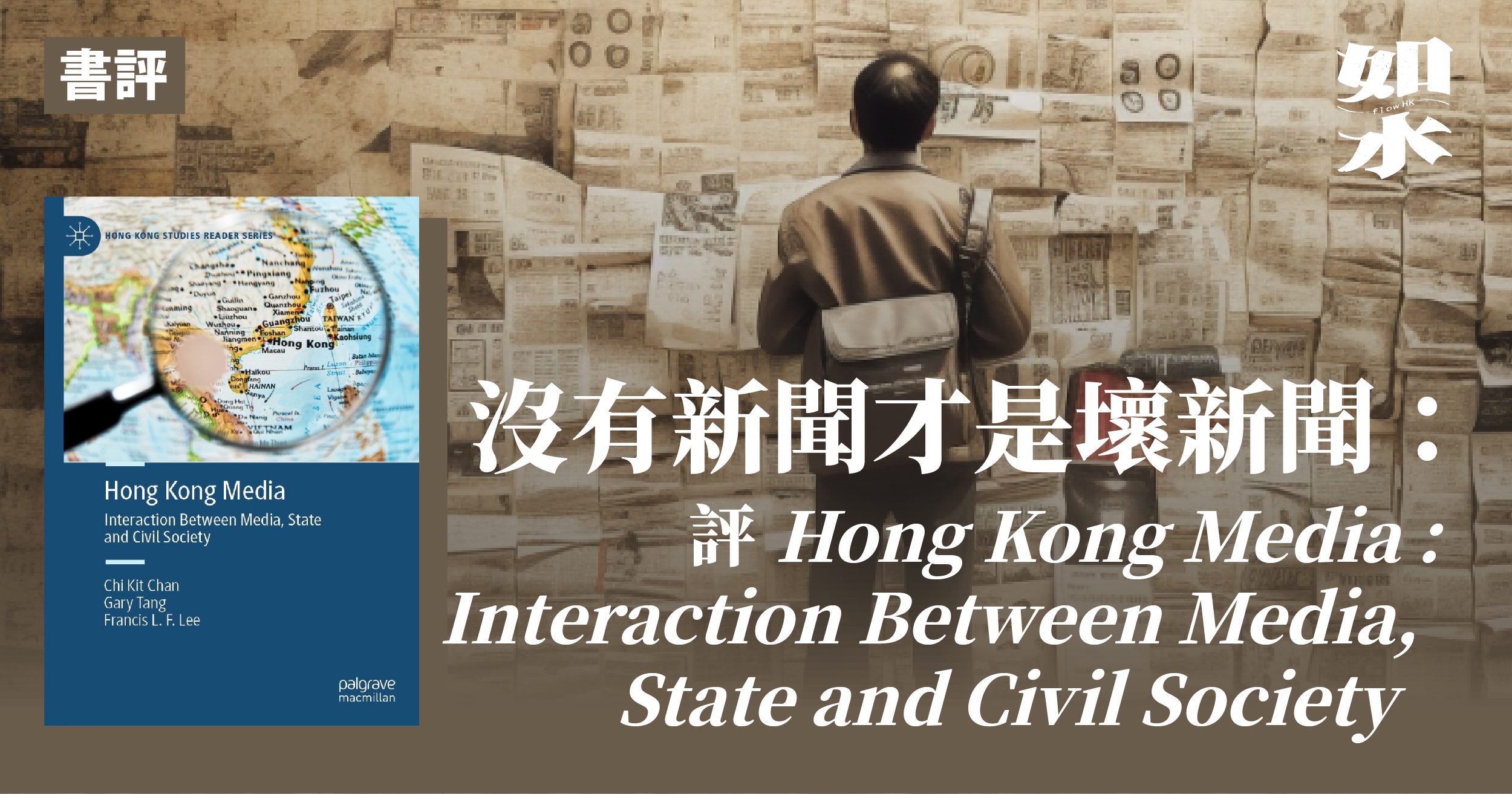
逝去的一種聲音?
2014 年 9 月 27 日早上 7 時,我站在金鐘夏慤道的便利店外,隔著玻璃看著當天報紙頭版。在我的記憶中,《大公》、《文匯》、《東方》等建制派媒體均形容,前晚衝入公民廣場為「暴力」行為,卻甚少提及警察當晚拿起警棍衝入人群追打示威者。反之,《蘋果日報》則提及當晚警察過分的執法行為。旁邊的友人與我徹夜留在添美道,他低聲喃道「只係得《蘋果》講真話⋯⋯」。這句話在當年相當諷刺,因為《蘋果日報》的新聞報道手法,在校園經常被老師詬病,甚至禁止學生引用。但在當刻的香港,似乎只有《蘋果日報》才把當晚示威者的經歷作完整報道。
2021 年 6 月 24 日清晨,100 萬份《蘋果日報》附上「給香港人的告別書」,被押解走入歷史。黎智英、壹傳媒行政總裁(同為《蘋果》社長)張劍虹、《蘋果》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等高層相繼被捕。不久後,《立場新聞》也逃不過停運、高層被捕的命運。在國安法之下,有一種新聞聲音在這些年間在香港被消失。不少網台 KOL 多次提及香港新聞自由被封殺,大眾如今須在海外尋覓具備公信力的媒體。經濟學家 Albert O. Hirschman 曾經出版一本書名為 Exit, Voice, and Loyalty。如今的香港媒體,是否已經失去聲音(voice),只剩下忠誠(loyal)和離開(exit)兩條路?
在西方社會有一句諺語叫「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No news is good news)」。但在極權社會中,的確是沒有新聞(news),因為只有好的黨國宣傳(propaganda)。當媒體只是黨國機器時,社會便缺乏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因此,在極權國家,其實「沒有新聞是一種壞新聞 (No news is a kind of bad news)」。那麼今天的香港,我們該如何理解新聞自由與媒體生態?這便是今期評論著作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要處理的問題。
新聞自由是「曾經沒有」 亦不是天長地久
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
本書回看媒體歷史,提到在初期的英殖香港,新聞自由曾經在高壓政治下處於低谷。例如,殖民地政府曾經在 1951 年訂立非常嚴格的報章註冊法例。雖然報紙業在當時非常蓬勃,但在報道殖民地政府及中英矛盾問題上,卻是敏感議題。例如在 1962 年 5 月的逃港潮期間,就有記者因在邊境採訪,而被控以「阻差辦公」罪。由此可見,當時的英殖政府並沒有尊重媒體監察政府的公權力。
然而,在六七暴動前後,港英政府逐漸脫離高壓政治模式,嘗試讓香港變成開放的國際城市。因此,新聞媒體逐漸變成資訊流通的重要媒介,也成為了公民社會的聲音。三位作者陳智傑、鄧鍵一和李立峯在書中提及主權移交前後的新聞媒體業,是介乎於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之間,有著監察政府和反映市民生活的重要角色。書中亦提及一些學者曾經預測,香港媒體於主權移交後,在後六四年代的中國極權治理下,會變成黨國宣傳機器。然而,這猜測當時落空,主權移交後的香港,親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媒體均仍擁有自由發聲的空間。
這種自由的空間在過去十多年的本土運動中,容讓不同本地媒體資訊流動自由,甚至產生動員能力。本書提到在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中,親建制與民主派媒體便發揮不同角色,代表著社會上兩種互相對立的聲音。而基於社會兩極化的政治環境,親政府媒體會與反政府的報道截然不同,前者甚至會為政府提供反對運動的說辭。而在網上媒體發達的年代,不少人把資訊接收的渠道轉移到網媒和 KOL,尋找代表自己政治立場的聲音。雖然在這段抗爭時期,不少人會質疑政見與自己不同的媒體的真確性,但在更廣闊的政治光譜上,「新聞自由」的確容許不同種類的資訊和視角,同時存在於一場運動和一個城市之中。
然而,如今不少人所惋惜香港逝去的「新聞自由」,其實是有一段歷史的限期,那大概就是六七暴動後的社會開放及國際化,一直到近年社運及國安法這段時期。學者推測回歸後「新聞自由」會完全消失,如今也是一種遲來的應驗。尤其當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非建制媒體逐一面臨打壓和倒閉。作者則認為,在後國安法時期的香港,新聞媒體的角色,和對公民社會的影響仍然有待觀察。
有新聞作為一種好新聞?
書中提及多項在國安法後收集的研究數據,其中提到在白色恐怖下,不少人減少在社交媒體分享新聞資訊,這減低了傳統新聞媒體的流通性。此外,網上的自媒體生態中,也出現「自我審查」的現象,例如留在本地的網絡 KOL 也減少在社交媒體發布政治相關的新聞消息。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新聞機構彷彿只剩下「忠誠」與「離開」兩個選擇。然而,我們仍然看見一些新聞工作者、旁聽師與本土研究機構,繼續努力在本地經營獨立報道並擔任消息發布的工作。這些人是值得尊敬和支持。此外,近年不少 KOL 和資深傳媒人選擇離開香港,於海外持續報道香港新聞及政治議題,成為「離開的一種聲音(Voice after exit)」。移民群體如何在外地建立全球性的僑民/公民社會?這也是近年流散政治學者熱烈討論的議題。
然而,本書在 2022 年 8 月發行,因此並沒有提及近年非常多人關注的《法庭線》和《庭刊》等本地網絡新聞媒體。這些媒體透過旁聽摘錄,把法庭內的內容傳播給香港本地和海外的香港人。這些報道客觀陳述為主,但提供了不少消息和新聞養分予海外一眾 KOL 及網絡媒體,讓事件可以持續發酵。例如 47 人初選案,在開審以後獲得全球各地港人關注,香港人在社交網絡不斷流傳、分享有關消息,亦有 KOL 和網民在網絡平台表達對法庭審訊內容的看法。因此,這些非政治取向的法庭新聞報道,仍在香港本地及海外香港人群體擔任相當重要的傳播媒介。
總結本書的討論,筆者認為海外媒體的成立,例如《光傳媒》、《棱角》、《綠豆》等,其實依然會對本地和海外香港人社群產生影響。當香港網絡依然流動,大陸防火牆尚未來臨之前,這些新聞消息和討論,仍會成為連結海外與本地港人的重要聯繫。因此,一天尚有報道香港的新聞,而非「宣傳」香港的「新聞」,這便是一則好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