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香港的政治啟蒙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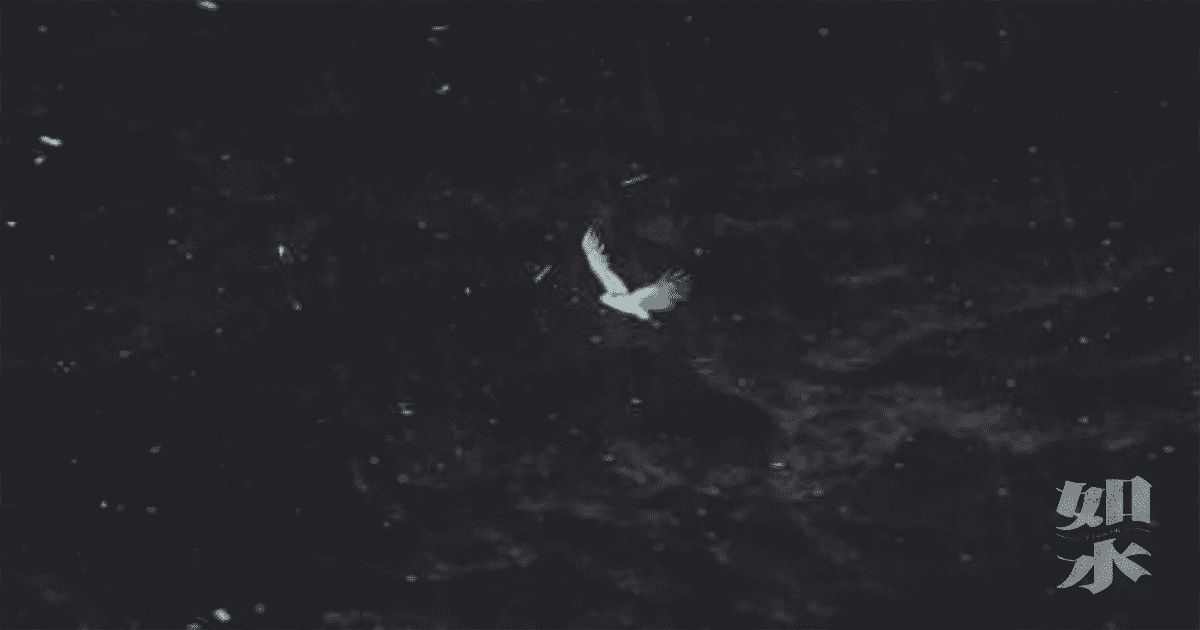
反送中—香港的政治啟蒙運動?
說2019年是香港社運及民主運動的分水嶺,或許不為過。在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大眾對社運的想像大多是以政治領袖所主導,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框架,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奠基的體制及承諾之下尋求進步及改變的抗爭。雨傘運動可說是第一個嘗試突破這些框架的群眾抗爭。但即使在雨傘運動中,大部分人仍是接受政治領袖所主導的運動,不接受在和理非框架之外的武力抗爭,而公民抗命最終仍是希望撼動政權去履行其普選的承諾,而與政權商榷的範圍僅僅是何謂真普選而已。到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卻取得了新共識。抗爭不再需要任何大台主導,大家可以不同的抗爭手段各自爬山—和勇不分、黃色經濟圈、大三罷、阻塞交通、國際線、裝修紅店藍店等,都已成為被廣泛接受及使用的抗爭方式。我們甚至開始形容自己已「輸出革命」,成為各地民主抗爭學習的榜樣。反送中運動彷彿就是香港人由抗爭「初哥」成長為抗爭達人的「啟蒙」運動。
但一年過後,不少人開始質疑:香港人真的成長了嗎?我們不再盲從政黨、政治領袖或明星,但卻一度過份相信連登等平台的權威,之後又奉不同KOL或外國政客的觀點為圭臬。我們拋開了舊有的行動框架,不再被和理非等規範所束縛;我們卻又「鬥黃」起來,以一系列準則去衡量自己及身邊人是否夠「黃」。我們看到不少香港人無私的付出以及勇敢,把自己的金錢時間甚或生命以賭注與政權博奕;但當我們嘗試推動全港三罷時,得來的回應卻是「我的訴求就是要返工」。一邊廂,我們以「兄弟爬山」等口號開拓了各種新的抗爭模式及戰線;另一邊廂,這些口號卻令我們在初選等需要統合戰線的時刻無法有效組織起來。是我們成長得太慢嗎?抑或是我們其實在原地踏步?又會不會是我們表面成長了,本質上卻仍然保留著所謂的香港人「劣根性」?
香港人所謂的劣根性,我們聽得太多了:香港人就是喜歡返工、香港人就是善忘、香港人就是自私自利、香港人就是只想買贖罪券的政治冷感動物等等。反送中運動刷新了我們對香港人、對政治、以及對抗爭手法及模式的認知。但與此同時,「Old habits die hard」:我們彷彿依然纏足於各種舊時代的思考模式、習慣以及規範之中,令我們的集體行動無法跟上新的認知。到底我們如何才可擺脫舊時代的詛咒,走向新時代的應許之地?我們可以再追問:擺脫舊時代的一切是否唯一的正確答案?反送中前的歷史,是否只是我們走向未來的「絆」腳石而已?
受新舊思考及行動範式交纏所困擾的,不單單是這代的香港人。環顧世界歷史,就不難發現類似的形勢比比皆是,而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歐洲的啟蒙運動。這場思想變革在十八世紀初揭起序幕並於該世紀末以法國大革命作結。在近一百年的歷史中,知識分子及抗爭者一直嘗試解答以下的問題:他們如何才能擺脫封建制度的魔咒而擁抱現代思想及價值觀?本文並不旨在重述啟蒙運動的歷史:啟蒙運動與香港民主運動時空不同,無法把前者的經驗硬套於後者之上。更有意義的是去看不同的知識分子如何去解讀、批判以及反思啟蒙運動,從而補足並豐富我們對香港處境的思考。本文將通過詮釋康德對啟蒙運動的解讀、黑格爾的批判、以及傅柯的反思,嘗試提出開拓兩條問題:
(一) 到底我們應如何看待種種新舊的思考及行動範式?
(二) 到底我們應如何思考香港人的本質、限制及可能性?我們這代人是已啟蒙,有待啟蒙,亦或無可救藥的一群人?
康德:何謂啟蒙?
十八世紀末,可說是歐洲啟蒙運動的最高潮,亦可說是其尾聲,但到底啟蒙運動代表什麼,在當時依然眾說不一。[1]在這歷史脈絡下,《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chrift)以「何謂啟蒙?」(Was ist Aufklärung?)為主題邀文,而其中一名撰文回應者為康德。啟蒙運動的核心對康德而言在於勇於自己作判斷的成熟態度,若然人類要改變其態度,則必需要相應的政治條件。
當時不少的知識分子把啟蒙運動與一系列歐洲的技術成就或一套全新的思考或行動範式劃上等號。康德在文中首句即否定這種觀點,並點出啟蒙的核心是我們脫離自身不成熟的狀態。一個不成熟的人就像一個不敢自己作出判斷的小朋友,凡事都要過問及依賴長輩或權威的意見。權威不一定是指人,也可以是宗教信條、神話迷信、法律條文、甚或社會規範。中世紀的歐洲人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不成熟:他們作的每一個判斷都要依附於政治領袖、教廷及教會、或羅馬法典的權威之上。康德的著眼點在於如果我說我今天覺醒了,那今天的我與昨天的我分別在哪?這分別不可能單單是我們換了一套思考範式,不論是從神權論換成社會契約論,抑或是從宗教觀換成科學觀—這很有可能只是以一套新的偏見取代舊的一套而已。所謂啟蒙,所謂覺醒,就是成長到能只靠自身的理智而不依賴權威作出判斷的階段。康德斷言這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態度問題:要自己下判斷,必需的不是過人的智慧或聰明,而是勇氣。畢竟,依賴政治領袖的判斷,出錯時歸咎於領袖則可,但判斷若是我自己下的,我就要承擔起錯判的責任。我若是要成熟起來,就必須要建立足夠的意志及勇氣,摒棄一切權威,靠自己的理智下判斷。啟蒙精神,可以一句口號以蔽之:「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
康德深明這轉變並不可能一蹴而就。習慣信奉權威的人,即使經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也不會發展出自我思考的成熟態度,只會以今日的權威取代昨日的迷信。所以康德指出,我們不應過分樂觀,這並不是一個「已啟蒙的時代」(enlightened age),僅是「啟蒙的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而已。此話何解?雖然人類還沒有脫離不成熟的階段,未走進「已啟蒙的時代」,但這個時代卻開展了讓人類成熟起來的空間,是「啟蒙的時代」。若然要把握這時代給予人類的應許,我們必須要建構並維繫相應的政治條件。啟蒙是一個社會需要共同合作才能解決的難題。叫一個習慣依賴權威的人自己下判斷,就像叫一個整輩子緊握著欄杆扶手走路的人放開扶手,他最終只會怕得徘徊不前。只有當他看到在他前後的人都一個個放開扶手並一步步的走起來,他才會開始覺得原來自己走路沒那麼可怕。所以啟蒙精神散播並紮根的基本條件是有一大群人共同並公開地行使自己的理智作出判斷。而這已假設我們政治上有足夠的言論自由:我們需要活在一個不會以言入罪,沒有言論審查的社會,我們才有向彼此展示各自的判斷的機會。這自然只是一個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而後人亦多批判康德對政治過於狹窄的理解,但若連言論自由也沒有,之後的亦無從說起了。
康德對啟蒙的解讀為香港的我們帶出以下問題:到底我們這一年來更換思考及行動範式,是否只是以新的偏見取代舊的偏見?我們在去大台後,是否掌握了自己作判斷的勇氣,抑或只是換了一批新的權威?
黑格爾:啟蒙的「真相」
對當時的歐陸知識分子而言,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代表啟蒙運動已勢不可擋,將改變全世界的政治及社會架構,而新政府在革命期間所頒佈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更是啟蒙精神的政治體現。所以當這場革命演變為雅各賓派獨裁下的恐怖統治時期,並以拿破侖的帝制復辟告終時,這些知識分子不禁撫身自問:到底是哪裡出錯了?其中一名嘗試梳理這個問題的是黑格爾。法國大革命對黑格爾意義非凡,他甚至在餘生的每年七月十四號都會與學生開紅酒記念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監獄;與此同時,恐怖統治時期政權的暴行以及人民之間的互鬥卻令黑格爾為之心寒。黑格爾於1807年在逃離陷入拿玻侖戰爭的耶拿市的同時,出版了其第一本重大著作《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2]他稱這本著作為哲學入門書,但這書名與該書的艱深程度可謂不成正比。這書之所以為「入門」書,是因為他梳理了啟蒙運動的歷史及思想意義,預備我們進入下一個歷史階段。
《精神現象學》對中一個章節題為「啟蒙的真相」。到底這真相是什麼?黑格爾斷言,當啟蒙運動拒絕一切教條、傳統、及規範,要求每一個人自己作判斷,運動自身亦失去任何確立自身範式的基礎,故此人亦失去作判斷的準則。啟蒙的真相就是其內在是空洞無物的,只能靠不斷批判現有傳統而延續。當現有規範及傳統被徹底推翻,啟蒙運動宣告完勝時,這場運動該如何延續下去?黑格爾結合其觀察及論證,指出這時運動就只能內部分裂並互相攻擊了。如是者,啟蒙運動雖則有其批判及歷史意義,但卻缺乏產生自身的規範及原則的能力,故此無法建構或維繫一套與啟蒙精神相應的政體及社會。根據當代哲學家Robert Brandom的詮釋,傳統社會的人通過把社會規範神化繼而對這些規範的普世權威深信不疑。[3] 啟蒙後的人理解到這些規範都是社會建構,有其時空的獨特性。這卻意味著沒有任何規範有普世權威,他們也沒有必然理由要接受任何規範的約束。但若然如此,他們又怎樣過一個道德人生,怎樣共同維繫社會?
若然法國大革命是啟蒙批判精神的體現,恐怖統治時期則是其空洞本質之後果。新政府不僅推倒封建帝制,更把所有社會組織視為封建遺物繼而一一摧毀,造成政府之下就只有個體化的市民的局面。更甚者,由於一切社會規範都被視為不再有權威的社會建構,在新社會中唯一有普世約束力的就只有整個社會的共同意志,而民主政府的決定就是共同意志的體現。黑格爾點出這只是假象而已—所謂共同意志,不過是在權力鬥爭中勝出的黨派的意志而已。理解到這一點的市民自然不願服從政府的決定,但對這新政府而言,這些市民卻成為對社會共同意志的威脅,是理應被殲滅的公敵。
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寫下《女性與女性公民權宣言》馳名的女知識分子奧蘭普‧德古熱 ((Olympe de Gouges))便因其在革命後鼓吹法國應舉行公投來,決定法國應選擇君主立憲制、共和制、抑或聯邦制,被新政府指控她攻擊革命政府及有復辟意圖,最後送上了斷頭臺。啟蒙運動造成了代表個體判斷的公民與代表共同意志的政府的必然對立,最終以血腥衝突收場,只是時間問題。
黑格爾在重構啟蒙運動時還帶出另一條路徑:也許是唯一一條既不用訴諸於權威又不用陷入特殊性的困境的出路,就是我們以效益作為新的普世原則。畢竟,效益看似是客觀可計算且普世適用的。然而,當我們只有效益這一條原則而沒有任何其他規範時,帶來的卻是徹底工具理性的思維:每一樣東西以及每一個人的價值也被貶成「他對其他人有沒有用」的計算,而「沒有用」的東西或人自然也沒有價值,輕則可以無視,重則應被整頓。其後法蘭克福學派在反思為何一個啟蒙後的歐洲會引發兩場世界大戰並猶太人大屠殺時,便是循這個思路出發。當人類失去其社會意義而僅僅作為經濟齒輪存在時,任何阻礙生產過程的人都理應被整頓掉,猶太人大屠殺只是這種想法的體現之一而已。引用兩名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及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講法:啟蒙的論證客觀地以瘋狂作結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is culminating objectively in madness) 。[4]
黑格爾對啟蒙的批判為香港的我們帶出以下問題:我們除了批判香港、中共政權以及過往的社運模式外,是否有一套能維繫一個新共同體的願景及組織,以及一套不止於工具理性的思考框架?
傅柯:再問何謂啟蒙
在1984年,亦即康德〈《何謂啟蒙〉》一文出版的二百周年,傅柯在再度以同一標題撰文:到底二百年後,啟蒙運動對我們有什麼意義?[5]傅柯觀察到他同輩的知識分子中,既有人依然堅信啟蒙運動的應許,但亦有不少人堅信我們必須全盤否定啟蒙精神才能從上述的種種問題中解放出來。對傅柯而言,不論前者抑或後者都已被啟蒙運動所綁架,陷入只能肯定或否定自身歷史的偽二元對立之中。所謂啟蒙,就是一連串塑造成今日的我們的歷史事件,而這些事件改變了社會及政治體制、技術與科技、知識形態、如何合理化各種知識及規範的方法等等,不論是肯定抑或否定,都改變不了這個歷史事實。我們理應去問更有意義的問題:這一系列的歷史事件如何定義了我們的存在、限制、以及可能性?
傅柯認為若要確切理解康德對啟蒙的看法,必須將其〈《何謂啟蒙〉》一文放在康德整套哲學體系中詮釋。的確,康德要求我們運用自身的理智去作出判斷。然而,康德並不覺得人可以通過理智解答一切問題。
相反,康德認為人的理智及經驗都有其限制,而嘗試解答超出人類理智或經驗的問題不單是沒有意義,更是極度危險的。但到底我們的限制在哪裡?康德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探討人類知性範疇去確定我們理智的限制,傅柯卻認為我們無法事前就分辨出什麼是人類必然的限制,以及什麼僅僅是歷史偶然加諸於我們身上的限制—這問題只能以研讀歷史及作出實驗性的嘗試去梳理。在研讀歷史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很多我們以為是必然、自然、和理所當然的社會現實及限制,其實都是一連串意外、鬥爭、壓迫以及抗爭的歷史偶然。若是如此,亦即這些社會現實亦不是自古以來的真理,也不必成為我們對未來想像的束縛。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隨意重塑社會。我們只能通過實踐作出各種實驗,嘗試一步步地轉化、踰越、或顛覆這些限制。一步全盤推翻這些限制是不設實際的,因為這無視了我們是活在歷史時空中,並因此被這時空所塑造的人。所以若然我們要活出啟蒙的態度,要做的就是批判自我—通過研讀自身的歷史,發掘歷史加諸於我們的限制,並作出各種跨越這些限制的嘗試。
傅柯對啟蒙的反思為香港的我們帶出以下問題:到底香港歷史如何塑造了我們種種的限制與可能性,我們又可以如何嘗試踰越這些限制?
香港的「啟蒙運動」
閱讀康德、黑格爾及傅柯三人對啟蒙運動的反思,如何幫助我們思考本文於引言提出的兩條問題?
我們的第一條問題是到底我們應如何看待反送中前後種種新舊的思考及行動範式?康德告訴我們啟蒙不單單是拋棄舊有範式並將其切換成新的範式。不論是把「和理非」換成「勇武」或「和勇不分」,都不代表我們的態度或精神有根本上的轉變。香港現今政治格局起伏不定,隨時都可以再發生巨變,舊有的一套固然不再管用,今天有效的抗爭模式也不見得會一直適用。也許我們可以向啟蒙精神取經,從而對「無大台」的態度作出更深刻的詮釋。無大台的根本精神,或許不在於無條件拒絕一切規範、組織以及領袖—這僅是另一套範式而已—而在於我們每一個個體都勇於擁抱自我作出判斷的態度。我們可以因應對時勢的判斷,時而參與無領袖的小隊抗爭,時而支持政黨,時而深化工會等種種組織。無大台的核心不在於組織及領袖的有無,而在於我們不讓這些組織架構抹殺個體的判斷。
但康德亦引出我們當下的一大困境:若然公民的啟蒙精神只能在可以暢所欲言的公共空間開花結果,那在言論自由日益收窄的香港,我們還能發展並保持自我判斷的態度及能力嗎?事實上,我們無法不承認政權的打壓的確會拑制我們發展公民德性的機會。正因如此,言論自由才是值得捍衛的權利之一。在此之上,我們亦應對身邊的所謂「港豬」持多一份同理心—他們的德性缺陷,某程度上正是他們成長於權威政體下的惡果。與此同時,我們亦不用絕望也不應等待政權的施捨。歐洲於啟蒙運動前或初期也不見得有言論自由:霍布斯的著作因得罪教會權威而被投之於炬,盧梭亦因言入罪落得流亡的下場。歐洲不少初期的沙龍,便是以討論文學及藝術為名暗中論政,從而逃過政權的審查。同樣,我們亦應嘗試以各種組織及方法去建構並延續屬於香港人的公共空間。這可能是影子議會,可能是公民議政平台,可能是不同的實體或網絡平台,可能是像這本雜誌的媒體空間,可能是以工作場所為本的工會,可能是以社區為本的區議會或其他民間社區平台,甚或是以個人社交網絡為本的種種非正規空間。我們只能不斷嘗試並檢討每一個空間的限制與可能性,在政權打壓之下保存及發展更多有利公民議政的公共空間。
我們不應以狹義理解何謂議政,只要是香港人關心的議題就值得討論。但在這些公共空間中,筆者認為有兩個頗為值得大家討論並共同梳理的課題,一為政治及抗爭倫理,二為我們對香港共同體的想像。
黑格爾對啟蒙運動的批評也是一個值得我們參考的警告:當一場運動缺乏對自身身份及規範的正面想像時,既可能陷入只能靠判批他者或內部分裂而延續的局面,亦有可能落入被工具理性所綁架的下場。過去一年,不少人對政治倫理的討論嗤之以鼻,以為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惟一值得討論的只有到底何種策略能有效打擊政權。但其實有問題的可能並不是倫理討論本身,而是太多既有倫理框架過於僵化。舉例說,「和理非」與「勇武」之間的取捨及調合是極有討論價值,但以往信奉前者的卻把後者完全剔除於考慮範圍(甚或指控勇武抗爭者為「鬼」),而信奉後者的亦視前者為行禮如儀的偽抗爭。反送中「和勇不分」的信念一改雙方輕視或質疑對方的風氣,但同時亦掩蓋了不少抗爭者之間實在的磨擦與衝突。
討論抗爭手法之間的道德取捨與合理性將給予我們一個妥善梳理這些矛盾的機會,但在此之上其實我們還面對著很多迫切的倫理問題。如果我們視彼此為手足,那我們對其他手足有什麼義務及責任?我們理應付出多少才叫履行了香港人的本份?我們在國際線上與其他抗爭者或政府是否只是互相利用的關係?我們是否有責任關心其他國家的苦難?即使是把視野帶回本土,我們應如何衡量各種社會關懷的重要性?工具理性只會問幫助受難的手足或各國的同行者是否有用,而這顯然並不足以解答我們的問題。除了政治倫理,我們還必須要問到底我們對香港人、香港共同體及香港未來有什麼想像?這並不是一個在抗爭全面勝利後才有意思的問題,因為這問題將左右我們抗爭及組織的路線以及對社會的關懷。的確,在過去一年間為了團結所有抗爭者,我們把這些矛盾擱在了一旁,但若未來要一起走下去,這將是一個無可避免需要共同商議的問題。
而當討論這些問題時我們無可避免地會觸及香港人的歷史。我們應如何詮釋這份歷史?其中一種主流論調強調香港的上一代只顧謀取自身利益而漠視政治,造成今天年輕一代不得不受苦的局面。這種論調基本上就是全盤否定傘運甚或反送中前的歷史。不管這論述是否真確,傅柯告訴了我們這樣研讀歷史也許沒太大意義。這時或許我們可以引入文首提出的第二條問題一併討論:到底我們應如何思考香港人的本質、限制及可能性?反送中運動刷新了我們對香港人的想像,正是因為種種嘗試均打破了我們對香港人功利並政治冷感的刻板印象。與此同時,不少失敗的嘗試卻加深了「香港人就係咁」的看法。大三罷的多次失敗,令人不得不承認或許「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就是返工」。
但這到底是香港人的必然限制,抑或是香港工會積弱、「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漏洞百出的勞工法、教育制度以及家庭壓力種種因素交織而成的歷史偶然?與其問香港人是否必然「就係咁」,或許更有意義的是去問:歷史如何塑造了香港人的限制,我們又可以如何嘗試踰越或顛覆這些限制?同時,或許我們也該視雨傘及反送中運動為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並去研讀這些事件如何重塑了我們,為我們打開了什麼新的大門,又加諸了怎樣的新限制。研讀自身歷史,可以防止我們過分美化或醜化自己及身邊的香港人,更立體的暸解香港人的限制與可能性,並為作出新突破而鋪路。
本文目的並不是要把啟蒙運動與香港民主運動劃上等號,亦不是要把前者硬套在後者的思考之上。然而,啟蒙運動的論述帶出了一個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一邊廂我們覺得若要突破今天的困境就必須摒棄舊有的思想及行動框架,另一邊廂我們卻發現自己無法輕易與這些舊有的思想、習慣以及規範切割。也許誠如康德所言,我們尚未走進「已啟蒙的時代」,但這正正是一個「啟蒙的時代」,而到底我們能否掌握這時代的應許,就在於我們面對歷史、面對自己、以及面對彼此的態度。共勉之。
[1] Kant, mmanuel. 1996 [1784].“An Answer to the 2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 Gregor, 11-2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Hegel, G.W.F. 1977 [1807].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Brandom, Robert B. 2019. A Spirit of Trust: 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2002 [1947].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and edited by Gunzelin Schmid Noer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 Foucault, Michel. 1984.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ited by Paul M. Rabinow, 32-50.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