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而非臺灣——作為中美對抗的最前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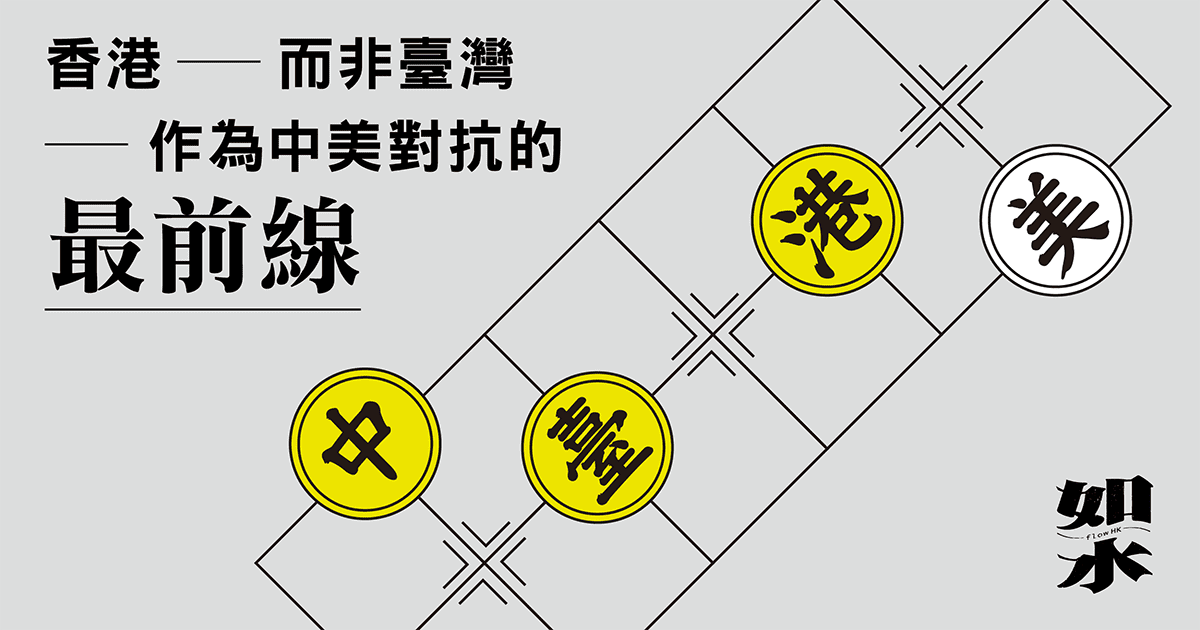
這幾年有幸認識了不少香港朋友。前幾年都是我關心他們,但這一年卻反了過來,常聽香港朋友關心我:「臺灣感覺變得好危險!」
我非常感謝香港朋友給我的關心,這種擔憂完全可以理解,舉凡今年以來引起話題的出版物,從 Chris Miller 的 Chip War 到 Hal Brands 與 Michael Beckley 的 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無不都是在討論以下這件事:中國與美國在經濟、科技乃至軍事上對抗,臺灣正巧在這對抗的中心,因此許多國際媒體便以「危險之地」來形容臺灣。
臺灣目前會讓人感到危險,顯然是出於中國在印太的霸權擴張,加劇了該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其帶來的影響有多個方面:第一,中美對抗的科技冷戰之下,臺灣的高科技產業不得不轉而注重地緣政治。第二,萬一爆發實質軍事衝突的「熱戰」,比方中國發動戰爭侵略臺灣,縱使臺灣跟中國隔著臺灣海峽,一場慘烈的戰爭仍會上演。根據 CSI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於 2023 年 1 月釋出的兵推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日本與美國若參與這場戰爭,多半解放軍會將戰敗,中國會損失多年建立的現代化海軍,臺灣則勉強取得慘勝,但經濟與社會仍不免遭受重創。第三,若臺海戰爭的結果比 CSIS 兵推更為不幸,最終沒辦法守下這場勝利,中國很可能會在臺灣上演紅色恐怖,國安、黑警與特務將與解放軍聯手壓制臺灣人民,臺灣人最終將喪失自由與民主。
不過,我最近愈想愈不對勁:從上面幾點衡量,香港不才是現在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嗎?畢竟,香港「已經」實質上處於比臺灣更加危險的境界。
首先,在國安法出爐之後,香港人進一步失去言論自由,並且有著隨時都會被秘密審判跟承受無期徒刑的風險。香港過去的自由民主,已大幅遭到限縮。我們可以想像,臺灣若被中國大陸實施國安法,臺灣版的條文將會大量取材自香港版。可是,這國安法之於臺灣,只是一條可能的世界線,在香港卻已實現。我認識的許多香港朋友,已親身感受到國安法的威力。
然而,本文想強調的,是另外兩種更深層的危險來源,即科技冷戰與實際上的熱戰。在這兩種衝突型態裡,香港——而非臺灣——其實才是中美對抗的最前線。這兩點,其實有不少香港人早已注意到了。香港抗爭陣營的民衆,可能會對於這篇文章接下來要闡發的主要論點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近年許多可見的運動策略,其假設便是建立在本文接下來要闡述的論點上:
在中美科技冷戰的對抗上面,比較少中國專家或美國學者觀察到(包含這些熱門出版物的作者),香港其實深深地嵌入到中國軍工複合體的經濟體系裡頭。大家不妨仔細察看美國近來對「中國軍工複合體」的制裁,有許多企業都跟香港有極深的關聯,比方說,在商用跟軍用都相當知名的商湯科技(AI 人臉辨識)跟大疆創新(無人機),都跟香港頗有淵緣。其他許多中國半官半商的企業,往往在發展過程中使用過香港提供的金融服務,也在香港公開上市以吸收市場資金。
除了科技上的冷戰,萬一發生了「印太戰爭」——也就是中國與臺灣、日本、美國等國家於亞太地區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戰爭,按照美國為首的盟軍處置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的歷史經驗,香港的金融業恐將被視為「協助戰爭與中國軍工複合體」而被視為中國侵略戰爭的積極協力者。
中國軍工科技公司的「香港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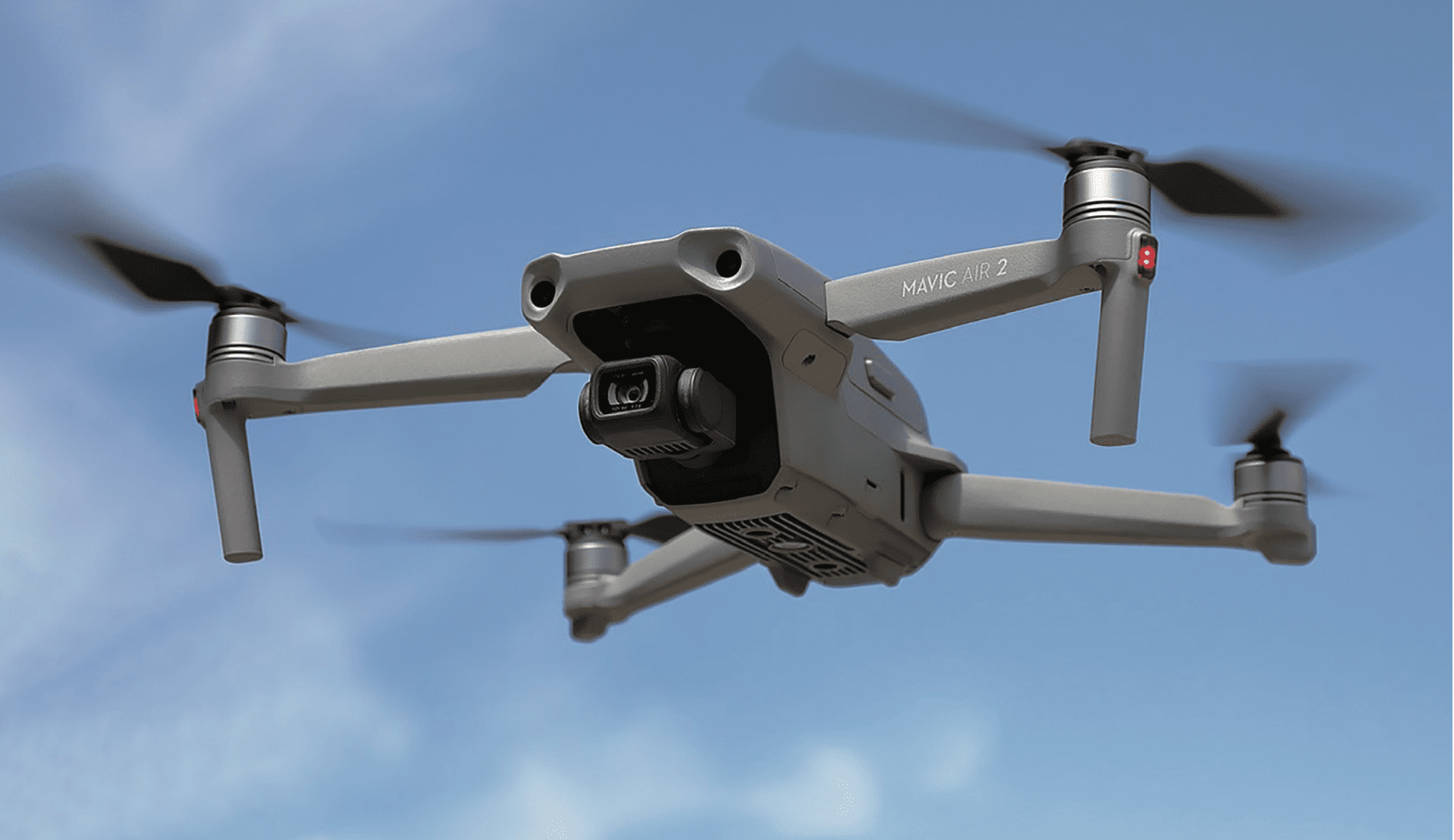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香港近年扮演了兩類重要的角色。第一是協助資金流通。香港整個經濟體於近幾年轉變成「中國的金融門戶」,促成了中國近年的「資本累積」。按照中國統計年鑑等等的資料,香港歷年來佔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約 60% 的份量,當中當然有許多外資企業是在香港掛牌,才轉而投資中國。除了引進資金之外,香港也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節點。香港仍然扮演了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最大的人民幣外幣中心,以及海外人民幣結算中心。在中國一帶一路事業上,香港是最佳的金融合作夥伴。整個香港便是一間巨大的金融機構,專門承銷全世界來往中國的金融業務。比方說,遭到美國制裁的商湯科技,便是於香港上市,而以無人機聞名的大疆創新公司,早年也曾得到香港的融資。
香港作為中國的金融門戶眾所皆知,但此外的第二個角色可能更為重要﹕香港的高等教育,是中國引進西方一線知識的重要基地。比方說,大疆創新的創辦人汪滔,曾經在香港求學,從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系畢業。汪滔曾經說過:「假如我沒有去香港,便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內地或去了美國,也不會創立大疆創新。」而商湯科技的辦人湯曉鷗則是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系的教授。商湯從創辦到現在,不少幹部跟員工,都出自香港中大的中國留學生。
大疆創新和商湯科技,都是美國制裁的重點目標。它們或許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隨著中國共產黨深入影響民間企業(比如阿里巴巴跟騰訊等),企業已經變成官方不分,一不小心就會「軍民融合」了。香港作為中國最大的融資基地,任何一間在中國擴張海外勢力扮演重要角色的企業,或多或少都跟香港的金融業脫不了關聯。
美國對於「戰爭積極協力者」的判斷:以二戰為例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方熾時,便開始思考戰勝日本、德國後,要如何有效避免法西斯復興。除了要解組日、德軍隊之外,美國許多的將領跟官員(包含麥克阿瑟將軍)都認為法西斯主義或軍國主義的存續,有賴其特殊的經濟基礎,在納粹德國,這經濟基礎是容克(Junker)地主階級跟大銀行家,在日本,則是財閥與無數的高階企業經理人。
盟軍如何改造戰後日本,正是我現在於哈佛的研究題目。在戰後初期,日本由俗稱 GHQ 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統治,由麥克阿瑟將軍擔任其實質政治領袖。麥克阿瑟雖然跟羅斯福不合,在日本卻與向來支持羅斯福新政的美國激進派官僚合作,推動日本「經濟民主化」,不只許多日本財閥遭到解組,被實施「公職追放」(也就是 purge),這大規模制裁的範圍,從公務員、政治人物、軍方,一路延伸到了經濟界,許多高階經理人也因遭制裁而離開崗位。
美國在二戰後,由於處理日本、冷戰、越戰、伊拉克戰爭等等的事情,累積了不少制裁經驗。比方說,現在美國國務卿 Antony Blinken 團隊裡頭,仍然包含了 Meghan O’Sullivan 等經歷了伊拉克戰爭並精於處理中東事務的老將。因為筆者並非白宮決策的專家,我不能肯定美國於二戰處置德、日的經驗,多大程度有所修正,但從美國白宮在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大規模地制裁俄羅斯商業寡頭(Oligarchs)可見,美國仍持「發動戰爭必然有其軍工複合體及金融跟經濟支柱」的觀點。

香港的深層政治經濟危機
分析這些東西,之於香港的朋友又有甚麼意義呢?
其實我想跟香港朋友說明,除了近幾年香港所經歷的政治問題,香港還存在著更為深層的政治經濟危機。這些危機,甚至比國安法來得更恐怖。這危機的核心,便是香港的經濟,早已深深地嵌入在中國經濟體中。在中國在亞太擴張海權並將影響力投射到全世界的過程中,協助紅色軍工複合體在世界各地資金流動的,便是香港和他的資本市場。中國的霸權擴張,與香港的金融業海外服務,已經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這表示,中國涉入的地緣政治風險,香港也將一同承受。
從經濟決策的思維來考量,風險當然可以冒,但問題是承受風險的同時,香港人得到了足夠的報酬嗎?若以整個經濟體的尺度來思考這問題,我們便等同在問:香港將自己過度與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擺在一起,是否得到的相應的經濟成長?當然,香港現在的人均 GDP 在世界上仍名列前矛,但跟 1997 年的光景比,香港不免失色許多:如果以世界銀行的資料計,1997 年香港的人均名目 GDP 約 27,000 美元,新加坡只有 26,300 美元,在 2021 年,香港的人均名目 GDP 約有 49,800 美元,新加坡則已經高達 72,794 美元,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物價,以國際購買力平價 PPP 來計算的話,新加坡 2021 年的人均 GDP 高達 116,486 國際元,香港約有 65,891 國際元,新加坡已是香港的 1.7 倍。
隨著中國加深了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戰爭一旦爆發,香港面對的危機可能來得又急又快。誠如上文分析,盟軍在戰勝後,便已計劃針對協助德、日的銀行家與資本家,進行大規模的制裁、解組與清算。現在香港的經濟體已經畸形地嵌入到中國的紅色經濟當中,如果歷史重演,中美發生戰爭,無論臺灣命運為何,我很難想像香港作為中國海外霸權最重要的金融樞紐,香港的金融機構與資產不會遭遇制裁,而這制裁的規模,很可能足與當年德、日金融家所經歷的相提並論。
換句話說,如果戰爭爆發,臺灣將會承受中國的飛彈,而香港則可能承受「金融核彈」。如果中國戰敗,則金融業可能會面臨大規模重整與「協力者清算」,這些戰時乃至戰後制裁的力道,會比現在針對香港上市中國企業的還要強上許多。
「黃色」經濟圈的困難與希望
從這一角度來看,維持黃色經濟圈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便變得十分明確了。香港與當時納粹德國與日本有一點極為不同,就是香港有「非藍」、「非紅」的黃色經濟圈。黃色經濟圈的經營當然極為不容易,許多是靠著香港小市民對於現狀的不滿來支撐的,但卻有莫大的政治經濟學意涵——黃色經濟圈實為一種「自救」,盡可能讓香港的本土經濟與中國的紅色軍民經濟脫勾。
本文剩下的部分,想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多談一點黃色經濟圈的困難與希望。
香港發展黃色經濟圈的一個困難,是香港政府並未實質獎勵和發展製造業。比方說,新加坡的政府於 1980 年代便觀察到過度發展金融業與旅遊業會有「過度依賴大國」的困難。因此,1986 年由李顯龍為主要發起人發表的經濟報告書 The Singapore economy : new directions : report of the Economic Committee,便將發展「新加坡本土」的高附加價值製造業列為重大目標。主打的高科技產業,要能善用新加坡轉口港地位,盡可能不佔空間但要有高附加價值。數十年過去,今天新加坡製造業,佔了新加坡 GDP 超過兩成的比例。
高科技製造業有兩點特色:第一是需要複雜的產業鏈。要有環環相扣的上下游廠商,比方說台積電在臺灣設廠,背後是有如家登、帆宣等規模不同的上下游廠商配合。第二點跟第一點有關,也就是高科技產業的產業鏈要足夠多元,容許具備高知識的創業者,一開始先開間中小企業,後來才把規模擴大起來。像台積電在臺灣的許多合作廠商,起家的時候也不過十幾人員工的小公司罷了,這跟金融業極為不同——十個人在今天地球上大多數的地方,都沒辦法辦一間新的銀行。
至於高科技製造業所需的土地,我們可以再拿新加坡為對照。新加坡跟香港一樣有土地不足的問題,但新加坡積極的利用裕廊集團(Jurong Town Corporation, JTC)等單位,興建新興的工業用地,並協助處理污染、廢料等等問題,進而積極招商吸引外商或新加坡年輕人來創設新工廠。另一邊的香港卻在土地管理上陷入失衡。香港房價極高,早期政府提出解決方法包括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的綠化帶,但民間環保與土地正義團體指出有許多閒置的「棕地」尚未開發,並建議香港政府把原有的棕地作業整合到單一大廈。爭執多年後,最近香港政府開始動棕地了,不過是打算將其轉換為居住用地,而不是提供鄉郊工廠的配套計畫。很多工廠未來可能要被迫關廠。新港兩地比較,表現相差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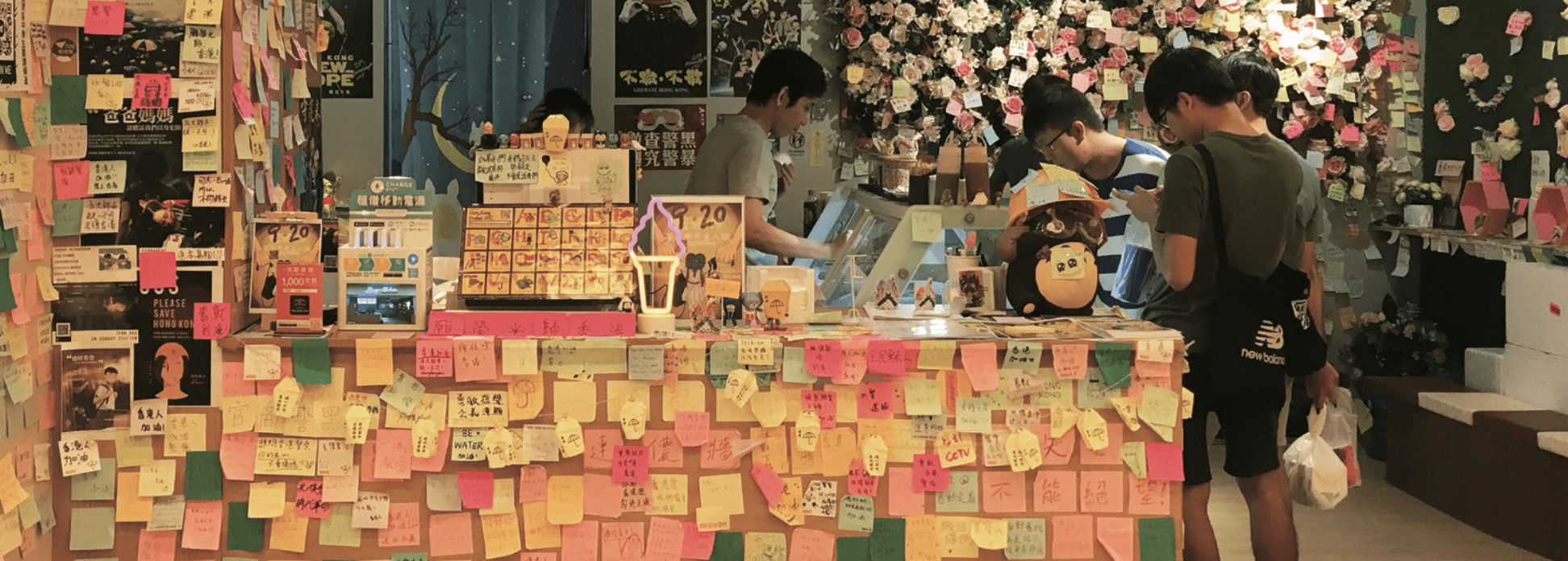
新加坡當然也有缺工的問題,所以政府也積極廣泛的吸納外國勞工(包括高技術跟低技術)來處理,然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底下發展的「深港澳大灣區」,卻反其道而行,是希望「香港人」成為輕騎兵,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跟工作,並未思考如何打造香港健全經濟體的問題。
也因為產業失衡,今天要在香港開「黃店」,多半要在市區靠實體店面或市集為主的服務業,但以黃色經濟圈在服務業的發展,還是遇上兩個困難:第一個是難與藍店競爭。藍店許多是勢力甚大的連鎖店,而黃店是由小市民經營、多半為合租經營的小店,但是我們都知道在市區經營的地租與人力成本極高,而連鎖店有透過擴張分店的「規模經濟」(或「密集經濟」)來降低成本的優勢1。於是,在高成本的經營環境,小店很快會被連鎖店殺下馬來;但小店如果跑去人口較少的地方,則連消費者都沒有。第二是,既然黃店的產業偏向集中,多以實體服務業為主,這種產業就難以協助幫助香港產業經濟的多元化,香港的產業活動仍會大量集中於整合到中國經濟的金融產業裡頭。
那麼,該怎麼辦?
當然,新加坡跟香港有一點極為不同。新加坡是一個主權國家。政府當局,要站在新加坡存續的危機意識下,規劃國家經濟政策。然而香港人只是一個民族,香港還不是一個國家,香港政府目前對於維護香港經濟體優勢的意識,可能比大英帝國時期還要低落。在大英帝國任職的各個殖民地總督,或出於個人積效表現,或出於殖民地英國紳商的利益,多多少少會實施保全自己殖民地優勢產業的經濟政策,然而香港近年來的政府,似乎只會把香港整合進中華帝國框架。
然而,這裡還是存在兩個救港的方向。
第一個方向在香港政府。政策的形成是極為複雜的過程。就算是在目前的香港政府,有企圖心的官員仍然可以出於自己的利益,積極提出有利於本土經濟的政策。例如戰後被國民黨統治的臺灣,就有國民黨官員如李國鼎出於自己的理想與仕途(當然不是出於愛臺灣),提出對臺灣發展有利的經濟政策。今天的香港政府應當要比當年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更有藥救一些。
另一方面,現在離散世界各地的「海外香港人」,許多還是與香港有著連繫。這些海外香港人不乏有本事者,能夠為香港連結海外各種資本與知識,一如過去海外香港人做生意的時候一模一樣。只是這一次,海外香港人要與留在香港的人合作,協助香港設立新的黃色經濟企業,作為「黃色資本累積」的過程。因為就算有國安法,就算在未來的科技冷戰下香港頻遭制裁,就算真的爆發武力衝突,香港人還是不能不吃飯、不去實現理想。長遠來說,建設香港非紅非藍的產業,也就是建造香港的民族經濟,就跟新加坡出於求存而發展自己的製造業一樣,是不得不為之事。
哈佛劍橋,是為記。
註腳
- 這文獻甚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Thomas J. Holmes 發表在 Econometrica 上的 The Diffusion of Wal-Mart and Economies of Densi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