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奶茶聯盟是國際連結的新範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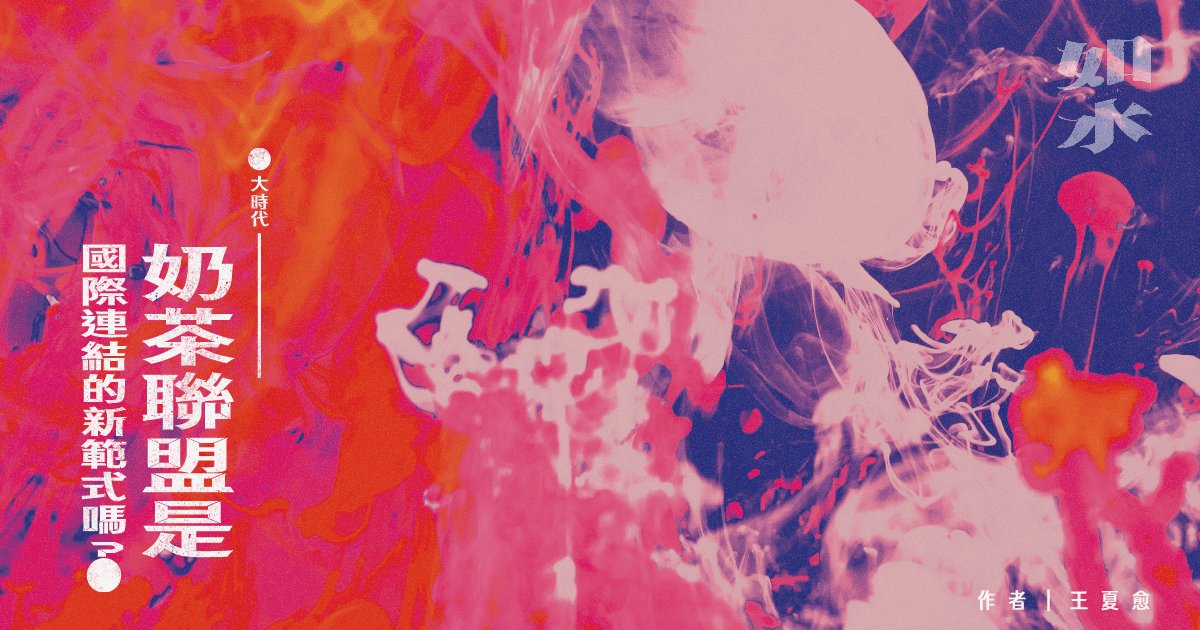
我們去連結其他民主運動,是為了達到什麼目標?
奶茶聯盟( Milk Tea Alliance )是非主流的跨國行動者網絡。除了廣義的民主、多元價值、反威權體制、及初期反中國霸權的情緒外,奶茶聯盟沒有清晰的政治議程,它亦未如一些國際環保或人道組織,各持份者有資金上的從屬關係。由 2020 年 4 月奶茶聯盟成形以來,筆者一直都很疑惑,究竟什麼是奶茶聯盟的黏合劑,令這個既沒有大台、身份混雜、沒有組織層級架
構、沒有實際政治權力的東西,繼續成為年輕東亞 /東南亞行動者連結的空間?在過去的十六個月,奶茶聯盟這個符號不單沒有過時,反而有更多國家的行動者加入。我們會直覺認為,政治能量和效益,是任何政治聯盟的黏合劑,沒有這些工具價值,聯盟則會瓦解。這篇文章會嘗試解釋,奶茶聯盟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下,其實沒有太多的政治能量和效益,但由於現有的國際秩序也面對認受性危機,反而滋潤了奶茶聯盟這種草根國際聯盟。
我記得許多年前,小學常識科教科書是這樣描述香港和中國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中央負責管軍事和外交,特區政府享有其他權力。」這個描述的潛台詞是,「 軍事」和「 外交 」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的行為,普通人在這兩件事情上是沒有角色的。事實上,不只是中國這類專制國家才會壟斷外交政策,我們在二戰後的國際秩序——聯合國、國際金融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是以國家作為單位,非政府組織( NGO )及學者只擔當著諮詢的角色,決策上還是要靠每個國家一票決定。貿易原則、多邊協議如上海合作組織、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這類經濟協議,也是用國家作為單位去影響彼此的農業補貼和貿易壁壘,甚至連制定國際勞工條約的代表團,都是由政府委派。1 雖然國際組織總把「 容納 」民間聲音掛在口邊,實際行使權力時,又是另一套嘴臉。
任何的民間國際連結,都不得不在這套國際秩序中遊走和尋找空間。遊說有權力的政客和國際機構,就成為很多民間團體的主要策略。很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會選擇專業化的路線,高薪聘請熟悉國際法的律師、研究員和說客,在國際組織的體制內與各國職業外交官打交道,或發佈長篇大論的倡議報告,嘗試影響他們投票的意向。商界則通過扶植智庫、大型經貿論壇,增強
政商界間的合作共謀。沒有資源的移民群體,會跟非政府組織合作遊說外交官和政界,聚居在民主國家的離散群體,亦可以善用族群身份政治,用選票來影響政策結果。
在這套以遊說和金錢為主軸的國際政治秩序下,奶茶聯盟是先天地不擅長遊說這種策略的。海外團體在民主國家進行遊說時,面對的第一大挑戰,是代表性的問題:海外團體需要通過找運動中的名人加持,或通過組織離散社群,以人數向遊說對象顯示自己的代表性。第二大挑戰,是如何令訴求變得精準 ——通過一條法案、增加一萬個難民名額、制裁某個實體(entity )、甚至在 Twitter上發帖子聲援。外交官、參議員這類政治精英公務繁重,愈複雜的訴求愈難明白,愈難明白的訴求就愈難得到支持。所以,離散社群通常都在運動內部,用相對時間解決內部分歧、建立共識,再向屬意的政治精英提出精準易明的訴求。
可是,奶茶聯盟偏偏是一個鬆散、由志願者維繫、沒有層級管理、亦沒有財力去籠絡政界的群體。奶茶聯盟的行動者來自五湖四海,只要認同民主多元價值的人,就能使用奶茶聯盟這個符號。要在這充滿語言障礙、文化歷史、政經脈絡截然不同的聯盟中,進行多輪的對話及建立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舉個例,今日的緬甸反抗運動中,以學生及工會為首的一派,傾向支持
全面攬炒 ——要求各國政府和商界全面撤走在緬甸的投資,切斷軍政府的財政資源。然而,文人政府前議員、少數族裔和民間團體組成的全國團結政府(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則傾向有限度的經濟制裁,盡量減低制裁對平民生計的影響。兩派都各自遊說國際組織和政府。在類似的立場和訴求上,奶茶聯盟是很難選邊站的。奶茶聯盟的積極參與者,例如不同國家的推特管理員,雖然有互相溝通合作,但大體上都是獨立運作,按自己的時間和志趣參與討論。當每次的討論都有人加入、退出、異議、提出新意見的時候,很難得出精準的訴求,並以此作為基礎跟政治精英進行遊說。
奶茶聯盟不擅長遊說,亦沒有金錢去購買影響力。有很多扶貧和義教的國際網絡,都是用「 撥款-做項目-吸引受助國政府參與項目-下一輪撥款 」的方式來維持合作關係及製造政治影響力。而國家則多以金錢外援( ForeignAid )和債務減免來影響他國政治和公民社會。2 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減免希臘的債務時,就迫使希臘政府重新設計退休保障制度、減少社會保障的支出,或調整其稅率增加收入等。奶茶聯盟的行動者掌握的社經資源本身就很少,較成功的資源共享例子,已經是台灣的行動者輸送防具給香港和泰國的抗爭者。在緬甸政變初期,軍方曾間歇性封鎖網絡,便有行動者發起偷運電話數據卡的行動,或替身陷險境的緬甸人在海外增值電話卡,讓他們可以跟外界保持聯繫。然而,直接援助的門檻其實很高,尤其是當泰國的抗爭者最需要的是疫苗而非防具之時;當羅興亞人在邊界需要的是人道物資而非網絡數據卡的時候,奶茶聯盟可以發揮的作用就很有限了。因此,只有國家級的援助機構、大型的人道 NGO、以及基金會等坐擁龐大財政資源的組織,才可以用金錢關係這套模式,跟受助國的公民團體建立長久的合作關係。
在常規的國際政治秩序下,奶茶聯盟這種劣於遊說,又沒有金錢影響力的跨國網絡,基本上是沒有吸引力的。但有趣的是,當常規的國際秩序面臨認受性危機時,反而讓草根行動者可以偏離原有的遊戲規則,來製造政治能力和影響力。
廣義而言,國際舞台沒有最高法官、沒有警察、更沒有上帝。這衍生出一個老問題,為什麼國家需要遵守國際規範和規則?如果有國家不守這些規定,又有誰可以擔當仲裁和執法者?至今國際關係理論亦未有( 亦應該不會有)定案。有些人認為每個國家都是以自肥為最大目標,有些則認為國家會以國內的民意為依歸云云。筆者傾向的理論是:國際秩序本來無一物,是不同國家約定俗成的習慣累積出來——例如「 任何國家都可以在公海範圍拘捕及扣留海盜船隻 」這條規則,是源於十九世紀歐亞國家不明文的習慣,至 1958各國簽訂《 公海公約》後,才正式成為明文的國際規則。同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成員制以及否決權,亦源於一戰前國際聯盟的制度。而安理會的超然地位,亦延伸到國際刑事法庭的制度:國際刑事法庭只能處理《 羅馬條約》締約國國內反人類罪行。國際刑事法庭如果要處理非締約國如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幾十個國家中發生的罪行,就需要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首肯。結果就是,違反國際人權規則得最嚴重的國家,要麼就不受規管,要麼就得到中國或俄羅斯撐腰,免受聯合國的懲處和介入。
有很多奶茶聯盟的行動者,都曾幻想過國際社會的介入,能夠為他們主持公道,阻止人權侵犯惡化。2019 年香港反送中示威初期,就有行動者在大型集會中,以多國語言朗讀宣言,表明爭取民主的訴求;行動者曾到訪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遊說,亦有人嘗試爭取國際法庭仲裁警察暴力的問題。一年前,泰國的示威者在世界人權日遊行到聯合國的分部辦公室,結果防暴警察用一重重水馬把聯合國辦公室圍起,驅散爭取釋放政治犯的示威者。在緬甸槍林彈雨的街頭,戴著建築頭盔、拿著油桶改裝成盾牌的示威者,盾牌上貼上“R2P ”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國家保護責任),呼籲聯合國阻止軍政府的種族清洗和鎮壓。結果當然是不成功的,而這些挫敗的經驗令許多人對現行的國際規範和機制失去信心。有緬甸的抗爭者就在推特諷刺道:「 聯合國你慢慢來吧,我們只是死了千多人,還有幾千萬的平民未被軍方殺害。」
民間社會對現存的國際機制信心大減,全球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升溫,亦在改寫二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以中國為首的威權陣營,已經佔據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近一半的席位,經常削弱譴責人權侵犯的議案,並利用數字上的優勢,阻止帶自由主義色彩的非政府組織( 例如維基百科基金會)參與聯合國機構事務。雖然《 世界人權宣言》九位的草擬人有中國的代表3,中國卻在近年大力推動西方人權價值觀不適用於中國的論述,並嘗試將國家主權和不干預內政的原則寫入國際規則。結果就是,連長期接受聯合國和民主國家援助的埃塞俄比亞,都敢於驅逐聯合國官員,指控他們干預埃塞俄比亞對提格雷亞的戰爭。國際機制無法向民間保證好的政治結果,威權國家衝擊舊有的國際規範,維護舊秩序的政治精英再沒法壟斷外交這個遊戲。
舊有秩序動搖,為奶茶聯盟這類跨國網絡開了新的缺口。當遊說政治精英和職業外交官的效益遞減時,人們開始用其他方法去影響國際政治議程。奶茶聯盟支援緬甸民主運動的策略可粗略分成數類:將庶民的消息和意見擴大,搶佔議程制訂的權力;增強民間行動者的認受性,讓被精英政治排擠的民間團體可以進入輿論中心;發動行動針對非政界的目標,切斷例如油公司、通訊企業對軍政府的支持。
社交網絡令庶民更易挑戰政治精英的話語權——例如東盟的推特帳戶只有14 萬追隨者,而奶茶聯盟( @AllianceMilkTea )、奶茶聯盟泰國、緬甸菲律賓和印尼合共的追隨者已經超過 14 萬這個數目。在推特上,抗爭者和公民記者都會在帖子上加上跟抗爭運動相關的hashtag,他們有不少人會把#MilkTeaAlliance 排在主要的hashtag 後,用以呼籲奶茶聯盟的行動者一起將消息炒熱,務求把現場第一手的見聞推上社交網絡熱門。
緬甸政變初期,聯合國依據既定原則,屬意東盟作為協商平台,跟緬軍討論停火和人道通道的問題。此舉當然惹來一片聲討,批評者指責東盟其餘九國同屬專制政府,他們只會包庇緬軍的行為。奶茶聯盟分別在四月和十月發表聲明,批評國際社會不應將緬甸的危機置於東盟處理,行動者亦以#ShameonASEAN,挑戰東盟的認受性,促請各國承認緬甸民族團結政府(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的合法地位。十月底,東盟高峰會決定不邀請緬甸軍政府的代表,象徵軍政府在國際社會的孤立狀態。
全球化模糊了傳統外交與「民間外交 」的界線。外交不再限於接見外國使節、簽訂貿易條款、處理領土資源爭議、軍事競爭等由國家壟斷的遊戲。科技巨企、跨國公司的商業決定,有時更能在國際政治中泛起漣漪。這意味民間可以針對更多對象施壓,影響國際政治的形勢。奶茶聯盟的行動者就嘗試針對美國雪佛龍和法國道達爾兩家油公司,以杯葛、直接行動及線上聲討的方式,要求油公司停止將利潤存入軍政府的銀行戶口。行動者亦協助整理緬甸政府外洩的密件,揭露跟軍方高層合作的外資企業,甚至兩日之內,將整套香港示威者的抗爭手冊,翻譯成緬甸文供抗爭者參考。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曾以「開源運動」(Open Source Movement )形容2019 年的香港示威,他指出,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在去中心化的狀態下,以網絡聚首一堂,商討、合作、貢獻自己所長。同質的開源運動同樣在奶茶聯盟發生,在短時間有效地向多個目標施壓。民意巨浪搶奪了媒體的注意力,亦促使政治精英加快回應速度,應付突如其來的民意巨浪。歐盟在十個月內,對緬甸軍方及其屬下企業實施了三輪經濟制裁,並準備在年尾進行第四輪的制裁。這種制裁的頻率,是過往難以想像的。
去中心化的跨國運動,亦令以往在自己國家單打獨鬥的行動者,開發出新的戰術——例如泰國王室長期濫用「 冒犯君主罪」( Lèse-majesté ),以年計的牢獄來懲罰批評王室的異見者。這令泰國的示威者只能用「 擦邊球」的方式在社交媒體批評王室。奶茶聯盟令泰國行動者可以跟國外的支持者合作上演裡應外合,國內的行動者先設定議題,再由國外的行動者製作尖酸刻薄、挖苦諷刺的 meme 圖,甚至組織行動者到泰皇下遢的德國酒店外,以投影機打出「把國王拉去坐牢」的圖像示威,突破泰國人長久不可侮辱王室的禁忌。
我們稍回到文首的引子:沒錯,國家和政府在法律上壟斷了「 外交 」這個領域,但事實上,每個國家對外的政治影響力,都因不同的原因被民間分薄了。奶茶聯盟的行動者,都在自己的國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但這個受打壓的共同體連結起來,竟然增強了彼此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既然沒聯合國、沒有一個議員代表、沒有國際大法官可以充當救星,就用群體的力量去組織杯葛、推動制裁、或摧毀某國某人的認受性等,去支援彼此的抗爭。這些手法未必百發百中必有成效,但行動與連結的過程,本身就是對行動者的充權,共同挑戰精英統治的舊秩序。
說了很多民間跨國運動可以如何幫助我們的抗爭,我最後想帶出一個問題:我們跟亞洲年輕民主運動行動者的連結,是否只有工具價值?如果跟他們連結沒有帶來政治效果,是否就不需要連結呢?我深信國際間的友誼,本身就充滿內在價值。社會運動內部存在張力和錯誤,需要反思、批判與和解,但我有不少時候,都不敢把這些張力擺上枱面,一來怕散播負面的情緒,二來怕增加運動內部的裂縫。國際的行動者友人在這個時候,就能夠成為最好的傾訴對象:由於大家都是社會運動中人,很容易就可以互相呼應彼此面對的困難;但由於大家都不在同一場( 狹義 )的運動,沒有重疊的利益與人事關係,所以都可以在平等與和平的狀態下解憂。沒有利害關係的對話,有時更可以點出彼此的盲點。
1.香港在 2021 年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的工人代表是鄧家彪,而中國的工人代表則來自中共直接控制的全國總工會。
2. 中國政府經常將這種外援行為抹黑成西方國家扶植代理人,和干預一國內政的行為。但事實上,Foreign Aid是所有大國都會使用的外交手段。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政府的金援行為有時更顯得詭異,例如捐助莫桑比克的 內政部、贈送物資給新聞機構、警察局,以遊學團和獎學金方式資助非洲國家的記者、婦女團體等等。
3.中華民國的代表是哲學家、戲劇家張彭春,被譽為「中國人權之父」,歷史考據認為他在草擬《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中,將儒家「仁」的思想跟西方自由主義結合,寫成宣言第一條的「理性和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