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水唔同兩孖仔 坐監出亡你點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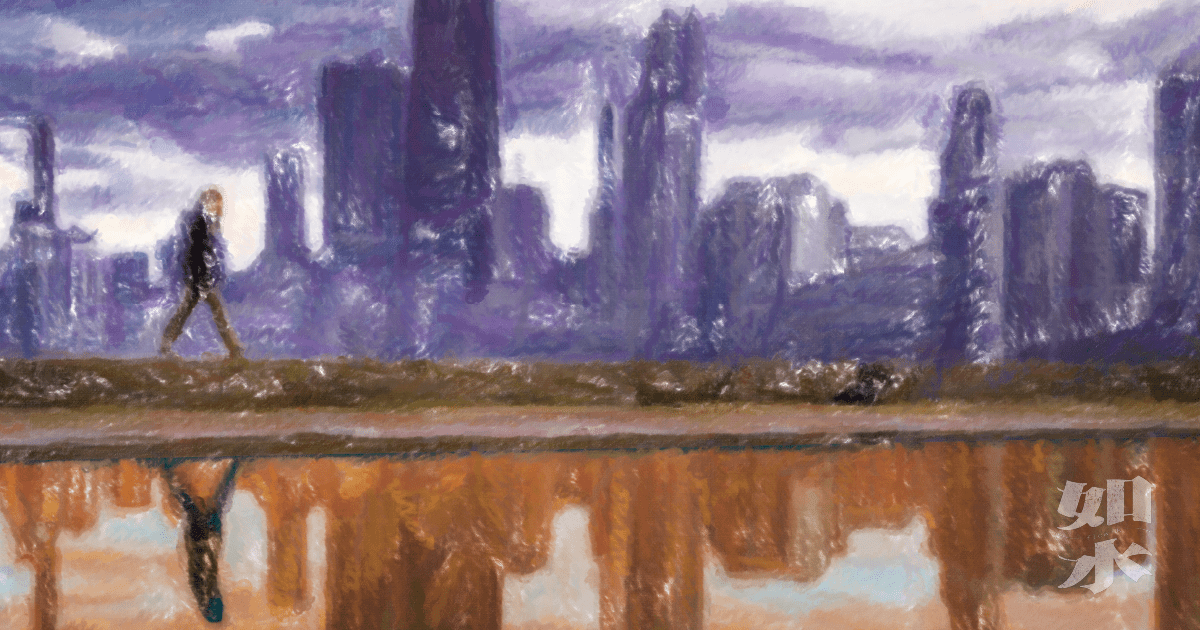
極權政府打壓之下,部分抗爭人被迫流亡,民主運動出現海外翼,這在國際上經常發生。我早前介紹過的西方現代流亡學始祖 Paul Tabori,他在 The Anatomy of Exile 一書裏説過,運動出現海外翼之後,緊接而來的是本土翼和海外翼之間的一些紛爭瓜葛,以及由之而來的運動内耗。糾紛處理得不好,等如給殺人政權送大禮;處理得好,卻能增進兩翼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分工合作。目前在香港運動裏的這個爭論,還是保持在合理的範圍以内,遠沒有演變成好幾年前本土派與泛民之間出現過的那種惡性衝突;感覺好像是一對孖生兄弟一旦分開了,際遇不同,回過頭來看對方,總覺得彆扭、不是味兒。本文主要探討處於兩翼裏的香港人如何正確分析彼此之間的關係、共赴時艱。
本土 v. 海外:困厄哪邊大?
我先作一事實判斷,解決一個可能出現的具體爭議:兩翼之間,那一翼的手足處境更艱難?需要比較的是兩翼裏我稱之爲屬於「 困厄組 」即所受困厄最為嚴重的那些成員。在本土翼而言,大體指那些現在或未來遭受或很可能遭受拘捕,或是正在審判過程裏、或正在服刑或服刑之後在學業、事業和家庭關係裏出問題的那些人。至於海外翼,主要限於那些沒有身份、學歷也比較低、倉卒間決定出亡以避酷刑的人。本土困厄組的處境不言而喻,海外困厄組需要面對的那種顛沛流離、不知命在何方的惶恐,卻是香港人因爲此前沒有經驗而不易理解的。當然,痛苦有一部分是主觀的,有些人泰山崩于前而不懼,另一些人的心理質素則比較薄弱;不同的人面對不同的困厄,也會有不同的適應能力,彼此感覺到的痛苦因而不能比較,所以上述兩個「困厄組 」都是以客觀條件定義。
兩種客觀的困厄都有一個高峰期。本土困厄,在刑滿獲釋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回落;海外困厄,於成功在某國取得合法居留身份之後了結。所不同的是,本土困厄不會完,共產政權之下,政治上你一旦是罪人,你永遠是罪人,直到或是你死或是他亡才終結,除非你也離開。此期間,你的學業和事業都無法簡單復原;你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政權的特別監視;若要延續抗爭工作,爲了不連累別人,你只能孤單地極謹慎地做,還得隨時準備再次遭到嚴厲打壓。
有此分別,所以有理由說,本土困厄組面對的艱難,應該是超越海外困厄組的。其實,這個結論,用經濟理論裏的「 隱性偏好顯示原理 」或者也可以得出,而且是連最切身的主觀因素也算計在内了。這個經濟原理很簡單:設 A和 B是兩個包含各自成本和利益的選項;如果你本來可以在 A 和 B之間作一選擇,而你選擇了B,那就表明對你而言,B 的困厄淨值比較低。海外困厄組的成員在出亡之前可以選擇留下進入本土困厄組,但沒有那樣做,那就顯示出,對他們而言,留下是更痛苦的選項。反過來説卻不成立:本土困厄組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
這兩個推論的結果,不約而同都符合「 一般人的直覺認知」,後者相當於普通法傳統裏的 Common Man Standard ,即以「一般人 」的良知水平作爲法律公義的一個標準。如果我們追求的是自由和民主,那麽,爲此目的而必須在不民主的政權之下失去自由,應該是最大的犧牲了。
因此,我認爲,在絕大多數情況底下,海外翼的人應該承認本土困厄乃更爲深重,海外的關懷和救濟資源應該較多向本土投放,而不是相反。這是我提出的第一個觀點。
( 本土翼非困厄組人士,縱然以後要處在極權統治之下,但如果小心謹慎,還是可以過比較正常的生活;海外翼非困厄組人士,因爲有普通身份、循正常渠道可以長居海外,縱有諸多適應問題,但都不妨礙他們過正常生活。我因此不在這兩類人之間作比較。)
去留之間:個體效率
繼此,我們進一步分析兩個更複雜的概念——道德和效率——以及如何容讓這兩個概念影響我們在「應該留下」還是「應該離開」之間作出選擇。分析的觀點也有兩個,一是個人的微觀的,一是群體的宏觀的。二乘二等如四,所以一共有四個思考題:
一、如何在一己的留下與離開之間作一道德上的取捨?
二、能否替整個抗爭陣營裏的人的去留作一總的道德判斷?
三、個人對運動的貢獻是留下大還是離開大?
四、為實現運動的最終目的,現在更多人留下有效還是更多人離開有效?
後二者是效率問題,比較容易分析,特別是第三題,首先處理。
思考這個問題,最好先有如下認知:有些不是不重要的因素,因爲根本無法量化和實證,是謂 imponderable ,不可能在任何人的理性算計之列。例如,個別國際游說項目的成效,理論上無法得知。某國決定制裁 X 囯,到底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考量的結果,還是你選擇離開到外國搞游說所以然,或者兩者的比重如何,都無法測度,哪怕游說者的外語能力和國際政治知識如何高超。又例如,在中港極權統治之下你選擇留下搞六四紀念,會不會比「前三十年」搞的更有效,而所謂有效,指的又是什麽,都是 imponderable。類似這種事,你要是有相應的魄力和優勢就儘管去做,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就是最好的了。其實,imponderable 的成分,或多或少存在於每一事情裏,做與不做,無可無不可,容讓相當高度的個人主觀,旁人無法也無容置喙。但我們可以肯定,這種主觀本身也是一種效率,因爲能夠在自己認爲適當的地方做自己喜歡的、認爲有意義也自信有成效的事,就會更積極投入。
更如果,你的去留決定是一些可知的客觀具體因素決定的,那你的決定無疑就更必然是在所有制約之下最好的決定了。總而言之,這第三題的答案因人而異,而都沒有絕對客觀的正確標準,每人按條件隨心所欲,雖不中亦不遠。原因是,儘管受體能、智商和情商的制約,人卻是優化動物,時刻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優化自己的每一舉動,如果你細心内自省,你就會發覺到這一條。
群體效率
第四題是去留的宏觀效率問題。學術上最能夠解答這個問題的,要算福祉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扼要地表述,這個理論認爲,在含大數目小個體的群體裏,當每個一體都按自身最大利益行事的時候,群體的整體利益也是最大的了。經濟學家論證阿當斯密的「 無形之手」的超凡效率,用的就是這個理論。
嚴格而言,這個理論是要滿足若干條件的時候才成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不存在「 外部效應 」。所謂「 外部效應 」,指的是個行事自利的時候,給別的個體帶來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比如説,吸煙、排放就是負面的外部效應; 1+1 > 2 的話,你和別的人的合作就有正面外部效應。一般論述認爲,如果這些外部效應相對强烈,就有理由依靠一個大台( 例如政府)强行限制或鼓動個體行爲( 例如用收稅、補貼、處罰、褒揚等干預手段 )。實際上,我們的確常常在市場裏看到各種各樣的外部效應,世界上的政府也的確作出這樣那樣的干預,但世界經濟還是基本上自由的,指令經濟裏的大台大規模干預失效而失敗的事實,二十世紀後半期已經大白於人世。因此可以説,實踐証明,便是「 外部效應 」存在於群體裏,容讓個體自由作決策還是最高效的。
同樣,我們可以把這個道理應用在香港無數民主運動人於兩翼之間作去留決定的問題上。基本觀點是,相對於既定的客觀及主觀條件而言,由個體自由決定去留,運動的整體效率是最高的。這結論便是加進「 外部效應 」的考慮,亦不會偏差太遠,原因很簡單。在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上,一己去留的確會產生外部效應。例如,運動一般强調凡事大家合作出力,簡單説,那就是 1+1 > 2,一種正面的外部效應;因此,如果我從本地抽身而去,餘下的手足就少了一些因合作而產生的額外力量。但別忘了如果我選擇離開本土,卻不像陶淵明那樣隱居不理世事,而是參加到已經略具規模的運動海外翼,那麽,我的 1+1 > 2 效應並沒有消失,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地方出現而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還有一個考慮也支持樂觀看法。大家知道,「 無形之手」如果遇到龐大壟斷體干預的話,就會失效,群體的整體運作效率就受損。2014 年之後,社運大台急促消失,到今天已經幾乎蕩然無存,社運界某種程度的壟斷體沒有了,「 無形之手」的本事,就可以盡量在社運裏發揮,上述結果因而更有可能在現階段成立。
那麽,如果有人宣揚一種特定的去留觀點,例如劉頴匡大力支持留下,或者歐文傑力竭聲嘶勸人離開,現在是不是都應該收聲了?當然不是。那是因爲他們都只是小個體,所説的話沒有大台的威力。相反,我倒是覺得他們的不同聲音,有助其餘的人在去留問題上深思,讓大家做出更堅實而正確的個人決定。
總的來説,在我們關注的形成了雙翼、沒有大台的社運場域裏,也存在著一隻高效的「 無形之手」,保證每個個體做出各自去留決定的時候,社運整體也達至高效率;大家見到有些社運人正在堅持留下甚或膽敢於此時回歸本土,而另外一些社運人正在束裝待發要離開,其實都不必擔心, 因爲都是那「 無形之手」正在運作,他們都是在流向他們各自能發揮最高效率的地方。至少,沒有現存的理論支持相反的説法。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道德問題。先講群體層次的道德問題。
去留之間:群體道德
群體選擇理論( social choice theory )大師 Kenneth Arrow 1951 年發表的兩個定理,首次嚴格證明了阿當斯密的市場「 無形之手」理論,成爲社會科學範疇裏的經典。他的研究成果從邏輯實證的觀點看,沒有置疑的餘地,卻受到來自哲學家的兩種批判。有關的議論,正好對我們正在討論的政治問題緊密對應。
批判之一源於一些學者質疑:「 效率」是人類行爲的最高準則嗎?Arrow 等人的回答很簡單:無論怎樣看重「 效率」,也不影響其他準則的引入;用最低的成本把餅造大了,之後你愛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總不會比只有一個小餅差。這個對市場的「 純效率批判 」,在大家關心的社運環節裏就更無關宏旨,因爲這個社運的唯一目標就是推翻暴政、光復香港,那是最大的公共道德,在這個問題上,運動的總體效率就是一切。
另一批判是,有人説,在 Arrow 的體系裏,道德根本沒有位置,他的理論不過是一個機械唯物的東西,充其量是解決了一個工程學的問題,與哲學家的終極關懷——怎樣的社會才是「 好社會」 (Good Society)——沾不上邊。Arrow 的回應非常有意思:他認爲他的理論説明,一個十九世紀以降的思想家們最關心的社會矛盾——資本與人的剝離與對立,其實是在自由市場裏徹底融和了;他的理論説明,階級絕對對立的看法是錯誤的,利益衝突的人其實可以很好相處,而「 無形之手」的效率正好提供了締造「 好社會」的物質條件。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齊藤直教授認爲,Arrow 的理論是邏輯實證與形而上道德的完美結合。 這個討論與我們關心的現階段社運大有相干。
自社運分成本土翼和海外翼之後,有關兩翼之間的重要性爭拗便起,引起一些摩擦和在更大範圍裏的焦慮,處理不好恐怕又會重複像幾年前本土和泛民之間的那種彼此猜疑甚至惡鬥,結果恐怕是兄弟鬩于牆、外不能御其侮。其實,這是古今中外政治運動裏經常出現的問題,以色列台拉維夫大學的Yossi Shain 教授在他的有關專著 The Frontier Of Loyalty — Political Exiles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裏,有一整章討論這個爭議,稱之爲「大分裂的政治」。不過,學術界對此卻不曾給出一個一般的理論看法。上面我的分析可以算是一個補白。在無大台這個時代前提之下,無數個體構成的社運「 無形之手」能最高效地解決本土和海外兩翼之間的人力資源分配問題;理解這個之後,大家知道去留爭議是不必的;整體而言,去留皆無咎。兩翼之間的融洽相處於是有了最大的個體實踐基礎和公共道德理由。
個體道德
餘下要探討的,就是上面列出的第一個問題:個人在去留之間,如何作一道德的取捨?我認爲,在純粹個人層次,道德問題是可能存在而揮之不去的,但不能讓這個個體問題與公共道德問題有絲毫混淆。上面説過,抗爭者留下,要面對的困厄一般要比離開更深重。因此,一個本來的戰鬥群體裏,一個手足選擇留下,自然值得敬重,而且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敬重;另外,一個手足選擇離開,心裏覺得有咎,那也是很自然的。但大家在個體層面裏感覺著這些道德張力的時候,不要忘記了「 整體而言,個體去留皆無咎」的道理。在外面的手足有内疚,那就不妨更努力利用比較寬鬆的海外環境去做支援本土抗爭的工作,化愜意為力量。兩孖仔同遮同柄唔同命,使命卻是一個。
本文的去留分析,是在大台已經不存在了的前提下才成立的。然而,大台也不總是無用的、錯的,她的確能夠在運動的某一階段裏產生一定程度的團結作用。不過,大台的最大缺點,我卻認爲是在於它取代了(或者説是擠掉了)個體的決策能力,養成運動中絕大多數人對「領導」、「大老 」們的依賴。如果民主( !)運動養成的是一大批只會按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做指定動作的個體,那麽無論這個大台是在本土還是在海外,始終都不濟事。現在我們要
觀察的是,大台消失之後,千百萬個運動人是否就失去方向失去動力;沒有了統一號召,他們會否就像沒上發條的玩偶。有跡象顯示不少社運人並不如此。無論是在本土還是海外,很多不知名而具戰鬥力的獨立個體或小群體都在積極運作,只不過,時日還十分短淺,他們的工作,特別是原創性的,困難特別多,一時之間還沒有很多具體成果可以看到而已。然而,關鍵的問題是,這些有自發性和原創性的獨立戰工群,到底是屬於海外翼的少數還是多數。這點現在尚不得而知。我們沒有理由悲觀,卻有龐大的道德壓力推動我們思考、奮鬥。




